纵使千山万水相隔,纵有诸般事务缠身,每一个远在他乡的游子无不会以“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会相逢”的永恒期许,慰藉浓浓的思乡之情。离开故乡的50多个春秋,每每午夜梦回,故乡青岛的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连同父母的殷殷嘱托,宛如一个个美丽的音符跳跃于我的心坎,激荡于我的军旅生涯。
几年前的那次返乡之旅,是铭刻在心的最近一次关于“家”的归属。走在小鲍岛充满现代化都市元素的街头,我努力寻找着记忆中的过往。当来到贮水山公园那修葺一新的台阶跟前时,岁月尘封的记忆闸门突然敞开,绚丽多姿、永不凋落而又刻骨铭心的“乡味”涌上了心头。当时我和我的小伙伴,每天都在这里玩,童年的记忆从一级级阶梯中纷至沓来。
小时候,我家住在贮水山下博兴路的一处大杂院,几十户人家拥挤在这座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二层破旧民宅,共用着一个公厕和唯一的水龙头。街坊邻居经年累月朝夕相处,彼此知根知底,关系融洽平和,过着清苦而平静的生活。
犹记得,老楼院的过道大概一米来宽,因为房间过于狭小,这个狭窄的过道便被街坊邻居征用,几乎每户都在自家门口处搭建了煤池子和能放开炉灶的小灶台,让本不宽敞的过道变得越发拥挤。但这也是老人饭后、孩子放学后离家最近的一处休闲娱乐场所。每当夕阳西下,上了年纪的老街坊在过道上边拉家常边压腿锻炼,像我这样的学生娃娃则在自己家门口支条凳子写家庭作业,而旁边便是母亲挥洒着锅铲子做晚饭的忙碌身影。一个大杂院,有熙熙攘攘,有安安静静,也有嘈嘈杂杂,充满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织变幻。
那时父亲的收入很低,生活物资匮乏,米面粮油等所有的物资供应皆要凭票证购买,家中生活愈发捉襟见肘。为了填饱肚子,我经常爬上贮水山挖野菜、摘槐花,去海边捡海带、挖蛤蜊……那时的记忆,恰似时而波光粼粼却又浪遏滔天的大海,激荡着童年的困顿饥饿,也孕育着新中国的百废待兴。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冬天,我背起行囊,带着青春的梦想,登上了前往云贵高原的列车。身后的小鲍岛渐行渐远,沿路熟悉的树木突然变得疏离。我时不时回头望一望,一种愁绪在心底慢慢弥漫、渐渐升腾,模糊了双眼。
记得临行前一晚,母亲五味杂陈地坐在小板凳上,默默地为我缝制一方枕头,针线活极好的母亲在这一晚却时不时被针扎着手指,心中似有千言万语,但却什么都没有说。第二天,背着那方装满了母亲爱与不舍的沉甸甸的枕头,我踏上了梦寐以求的从军之路。
这一步迈出去,便是半个多世纪。从此,家乡变成了夜深人静时我在西南边陲的浓浓思念。此时此刻,坐在窗前,望着眼前这杯清澈醇厚的茶,我想转身仔细端详那段过往,但我却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呼唤,再也看不到那慈祥和蔼的双亲,再也找不回那个不停奔跑、无忧无虑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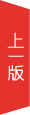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