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
话剧《惊梦》是陈佩斯继《戏台》之后的又一部诚意之作,透过昆曲大班和春社在战争年代的一段经历,表达了一个回味悠长、悲喜交织的主题。在话剧舞台上表现昆曲戏班的故事,本来已是戏中有戏,而故事所处的特殊年代、《牡丹亭》与《白毛女》的双重变奏又使得戏外有戏,意蕴堆叠。
戏班子里故事多,昆曲作为雅中之雅,历来受到士大夫们的热捧。一直到了民国时期,许多家境较好的家庭还会把“拍曲子”作为一项重要的技能,要家中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掌握。昆曲之雅,在于她集正统古典的诗词文化于一身,行腔、音域、起调、身韵,作为舞台艺术的各种元素,无不体现出中华美学的气韵。而传统之美又是脆弱的,正所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在离乱的年代,如何将一出《牡丹亭》唱下去?这道理解放军司令员秦向诚懂。他在少年时就听过和春社的戏,手里还存有老班主签名的戏单。正因为他是行家,和春社的一班人才得以正名。虽然有一位乐手穿了国民党的军服,但行家秦向诚非常确定地说:“这就是一个戏班子。”一句简单的话,却让人五味杂陈。
“戏班子”是一种浓缩了的文化形态,童孝璋和他的和春社信奉一套经历岁月洗礼的规矩。“世道乱了规矩不能乱”是童孝璋口中的“名言”。上至帝国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有了这规矩,童孝璋就以为可以从容面对一切。但是一头撞进战事的和春社,规矩是坚持不了的,他们得吃饭,得活着,这个矛盾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
当《白毛女》的剧本拿来时,第一轮冲突就呈现了。1945年首演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歌剧《白毛女》现在已经是民族歌剧经典,而在当时, 这部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和春社所不能接受的。剧本中的戏文“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唱腔的设计“看起来有点像梆子”,那得把嗓子横起来唱。柳梦梅变成大春,杜丽娘变成喜儿。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一下跳跃到“恨似高山仇似海”,其中的变化充满了错位与误解,也就充满了戏剧性。乐队在用丝竹演奏似是而非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三姐为喜儿定了全是“苏工”的白色戏服,而大春既然是大武生,就得是插着护背旗的赵子龙。相信所有的观众在三姐精心设计的喜儿与大春呈现在舞台上时,都会哈哈大笑。错位与误解造成了奇特的喜剧效果,而当解放军战士把从老乡家借来的衣服从包袱里拿出来时,冲突摆在了桌面上。“《白毛女》不是一个古代的戏”,与“上次去上海看完文明戏,您可是数落了一路”,喜剧的外壳下包藏着的是一个难解的题。谁都没有错,可是问题如何解决?
一部戏的核就是冲突的生成与解决。第一轮演《白毛女》的冲突,依靠的是秦司令对于两种艺术形态的正确把握。“我是真想静下心来听一出‘游园惊梦’,可是现在我们的战士需要上前线打仗。”而在和春社内部,也早有乐手读完《白毛女》的剧本后,感动得放声痛哭,因为他的父亲与杨白劳遭遇相同。在这两重铺垫下,和春社的“白毛女首秀”大获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舞台上,这一段的表现特别有意思,喜儿与大春并没有真正出现在舞台上,而是借用坐在台阶上观看演出的三姐、何广顺和常少坤的对话来实现。这是话剧里虚实结合的手法,推进了叙述节奏。战士们山呼革命口号时,把三姐吓坏了,当明白这是他们为剧情所感动时,她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这样叫好的。
在《惊梦》里,《白毛女》与《牡丹亭》的交互出现是重要的冲突。这是戏中之戏,而戏外的戏则是来自陈佩斯的。陈佩斯的父亲陈强先生是第一代黄世仁的扮演者。有个真实事例——由于陈强演黄世仁太像,有一位小战士想起自己家的遭遇,一时间分不清舞台与现实,居然对着陈强举起了枪。这是《惊梦》里的情节,也是陈佩斯向他父亲致敬的方式。班主演活了黄世仁,像是在说一个朴素的道理,不管是昆曲还是所谓的“梆子”,演得好才是硬道理。《惊梦》好评如潮,与陈佩斯等演员高超的演技是分不开的,他们虽然不是戏曲演员,但是经过了昆曲的严格训练,把一个戏班子演得活灵活现。
《惊梦》里的人物关系是复杂而多重的,秦司令与谭世杰这对黄埔老同学本来有着同样的爱好,同样的志向,却因各自的处境兵戎相见;何凤岐与童佩云本是青梅竹马,但凤岐的父亲却一门心思让他去香港当少东家;常少坤虽然是地主家的少东家,一无所能,游手好闲,却是个心地善良的戏痴……复杂而丰富的人物关系,使得剧情层层叠叠,冲突延绵不绝。两个多小时的时长几无一分钟的闲情,舞台上像是织起了一层绵密的大网,网住了所有剧中剧外的人。
如此饱满的一台戏要怎么收场呢?戏楼里重新唱起了《牡丹亭》。因为“不能把这些文脉断了”。“各位,和春社伺候大戏《牡丹亭》三天三夜,与看官同乐”,此时漫天飞雪,百般滋味都融进了游园惊梦里。
作者简介:张彤,作家,资深媒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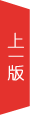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