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欢
诗性成就诗人,人性决定诗性。怎样的人性才能成就伟大的诗人?翻开张炜的《唐代五诗人》,或可一窥究竟。张炜是山东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唐代五诗人》是他最新的文化随笔集。
《唐代五诗人》从唐代诗人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的生平讲起,追寻他们各自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探究生命特质是如何影响诗人、成就诗人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王维描写自然山水的诗作很多,他的佛性令他的诗境清寂超脱。但是,王维超然的诗性离不开“辋川别业”这一物质现实的存在。正如托尔斯泰有雅斯纳亚大庄园、罗望山庄是福克纳的精神领地一样,“辋川别业”也是王维的安身立命之所,让他得以侍奉母亲,过上亦官亦隐的生活,写出空灵淡远的诗作。
“辋川别业”在辋川山谷,规模宏大,面积约有七十平方千米,内有华子冈、文杏馆、鹿柴、白石滩、漆园、椒园等二十处景点。王维苦心经营“辋川别业”,一是为了安顿母亲,让母亲单独拥有一处礼佛之所;二是为了大隐于山林,是一次成熟的人生选择。“辋川别业”的存在,令他的隐居生活无忧衣食,有别于陶渊明亲自耕种、为柴米油盐发愁的窘迫境地,从而成为古代隐居人士的模范标杆。在此居住十六年后,也就是王维去世前几年,他居然将“辋川别业”献出,改作佛寺,每日只“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一切归于虚无,他的生命也进阶到一个新的高度。
都说“文如其人”, 韩愈性子急,火气大,诗文同样气势磅礴、雄伟峻奇,常常下笔千言,滔滔不绝如千军万马。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高度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有高度的自信,他的视野超越了时代,他的“人生起伏动荡,诗文也就更加浑茫,有极耐穿凿的硬度与厚度。”
韩愈的代表作有《送李愿归盘谷序》《师说》《原道》《谏迎佛骨表》《苦寒》《送穷文》《鳄鱼文》等。其中,《谏迎佛骨表》致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险遭杀身之祸;《送李愿归盘谷序》令苏东坡赞不绝口,被尊崇为唐代唯一的好文章。
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有诗作两千八百多首。他是一个多元混合、矛盾繁复的诗人,既写出了许多揭露时弊、体恤民生的诗句,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新乐府·卖炭翁》),又写出了许多哀怨幽婉、情意绵绵的文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
但令人惊异的是,白居易很不看重自己的代表作《长恨歌》,甚至不愿将它收入自己的诗集。令人不禁联想到因《变形记》而享誉全球的一代文学宗师弗兰兹·卡夫卡,他生前一直认为写作是一种诅咒,甚至想在病逝前销毁自己的所有作品。或许正因他们人性中的矛盾冲突,才能写成流传千古的佳作。
杜牧家世显赫,虽然祖父官至宰相,但他生不逢时,仕途不畅,一生都被定格为“青年才俊”。其诗风率真明快、精美剔透,一如那首《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李商隐的诗风清丽幽绝,《锦瑟》最负盛名:“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此诗虽华丽缠绵、意象朦胧,却又晦涩难解、伤感隐秘,恰如他的性格,既有悱恻多情的一面,也有壮怀激烈的一面。
《唐代五诗人》是一部精彩的古典诗论。张炜从哲学、诗学、美学和文学等不同角度,对五位诗人的诗句和诗风给出了见解独到的点评,并一一指出其盲点。他盛赞韩愈的壮阔文辞和充沛真情,认为“语言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辞章连缀功夫,而且还深刻连接着生命的激情和力度”。他批评白居易的很多诗可有可无,认为他的所谓“癖”与“魔”,其实是一种写作惯性,是一种不能遏止的劳动欲望,这对于诗人的多产是有利也是必需的,而对于生鲜动人的创造,则往往是一种伤害。
《唐代五诗人》适合慢读细品。张炜的文字质朴实在,不囿于浮光掠影地点到即止,而是力求讲得通透明白。他将五位诗人的人生轨迹和诗文名篇逐一对应,从情与理、人性和诗性上品味诗人,为我们烹就一壶回味悠长的清茶,令人击节叹赏。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东坡就说过:“其文如其为人。”诗文的品质映照人性的质地,要学作文,先学做人。因为,生命的诗性、纯粹性,并不是后天习得的,而由一个人先天生命的性质所决定。人性决定诗性,诗性成就诗人,当个人心灵回归之际,也正是诗性洋溢和观照人性之时。
作者简介:乔欢,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深书评人。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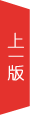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