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花
那一年,我七岁,母亲三十九岁。秋夜凉如水,我突然发起烧来。母亲摸着我滚烫的额头,急急地背起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乡里的卫生院。我伏在母亲的背上,听着远远近近的虫鸣声,听着母亲粗重的呼吸声,把脸埋在母亲发间,摩挲着。母亲头发间那熟悉亲切的味道,让我心安,慢慢地进入梦乡。医院里,母亲安抚着因打针疼痛而哇哇大哭的我,灯光下,瞥见母亲的黑发间有一丝白,格外刺眼。是不是一阵又一阵的秋风,吹落了叶子,也吹出了母亲那根白发。我轻轻伸出手,拔掉母亲的白发。在我幼小的心里,母亲不会老,永远是眼睛明亮,头发乌黑的模样。
那一年,我十七岁,母亲四十九岁。暑假过后,在百里外的城市读高中的我要返校。母亲早早起来,生火、合面,给我做饭。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地响着,母亲忙着切菜、擀面,还不忘往灶膛里加几根木柴。一会儿工夫,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了我面前。母亲做的,依然是我最爱吃的浑汤面。杂面条、芝麻叶、花生碎、黄豆、碎芹菜,这些普通食材,经母亲巧手烹调,在我的眼里,是难得的美味。我低头吃着,香味在舌尖打个滚,便落在心上。阳光里,我抬头又看见母亲的白发。乡下忙碌的日子,稠得像树上叶子,我不知道母亲的缕缕白发是哪一天长出来的,只是被那星星点点的白刺疼了眼睛。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母亲五十八岁。唢呐声声,《百鸟朝凤》的曲子欢快喜庆,吹落母亲的眼泪,也吹疼我的耳朵。这个特殊日子,亲友们围着我,祝福声声,笑语连连。唯有父母沉寂无言,母亲穿着大红的衣服,和父亲一起端坐在藤椅上,接受我们的拜别。出门时,母亲拉着新姑爷的手,半天才说出了一句话:“我把闺女交给你了,好好待她!”朦胧泪光里,俯瞰着母亲,她的白发似乎更多更密了。那个秋天,忙碌着为我张罗嫁妆的母亲是沉默的,沉默如田间丰硕的庄稼。母亲默默地给我缝制喜被,真丝被面是她托人从杭州买回的,大朵大朵的牡丹花争相怒放,摇曳生姿。母亲想说的话,都缝进了密密的针脚里。
那一年,我五十岁,母亲八十二岁。女儿上班时不小心崴了脚,我和爱人接到电话,一刻也不敢耽误,开车赶到省城去接她。看到女儿的脚又红又肿,我心疼得直掉泪。接下来的日子,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女儿身上,一趟趟带她去医院,一次次给她买各种她爱吃的水果和零食。周末早上,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母亲。母亲用手抹着额头的汗水,气喘吁吁道:“我来看小雨,她的脚好点没?”我呆住了,不知腿脚不便的母亲,走了多久才到我家的,也不知母亲费了多大力气,才上到我们家四楼的。我的心如被针尖划过,瑟瑟地痛。我只顾忙女儿的事情,好久没回家看父母亲了。母亲回去时,我送她去车站。母亲老了,她那一头的白发,如风中的芦苇,摇曳在我的泪光里。
白发那么近,时光那么远。在一程一程的光阴里,母亲的爱如影随形,陪伴我走过清风艳阳,走过雨雪风霜,走过无数个日出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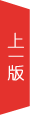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