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
芦苇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初冬时节,有一点微微的凉意,母亲一个人弯着腰,在芦苇地里割芦苇。微风吹着鹅毛般的苇絮,也吹着母亲花白的头发。
一年又一年,芦苇站起来,又倒下去。
那一年,我决定把我在村子里居住了十几年的土屋卖了。与父母商量,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也没有说什么。
那已经是我搬到县城居住很多年以后了。那几间土屋一直闲置着,被风刮着,被雨淋着,被岁月侵蚀着。
卖土屋那天,买主站在天井里,我们也站在天井里,商量都能接受的价格。母亲说,我们卖屋,不卖宅基地,房前屋后还都是我们的。
我们小村居住十分分散,一家一户的,隔得很远。我和东邻隔着十几米,与西邻隔着三四十米。
我家房前有一片荆条,屋后有一片芦苇。母亲最在意的是屋后的那一片芦苇。
买主是我的西邻。他买屋不是居住,也不是为了那块宅基地,而是那几间屋,可以当鸡舍,以便于他扩大再生产。那几年,他在村子里孵化小鸡,在附近村庄小有名气,销路顺畅,他想扩大规模,就看上了我们闲置的那几间土屋。
几年过后,他的儿子去了青岛工作,没多久,他也去了青岛,不再做孵化小鸡的生意。他自己家的房子舍弃了,我家的土屋也舍弃了。没有几年,风刮日晒的,他家的房子和我家的房子,都成了危房。
当时,三间土屋很便宜,卖了1000元钱,等于白送。但土屋闲在那里,没有人居住,比人的寿命都短。人住在里面,有烟气托着,屋子不会倒,可以住几代人。屋子怕空,一空就像人的孤独,熬不了几年,说完就完了。卖了,给买家有更大的用处,也是给那几间土屋的生命的延续。
我屋后的那片芦苇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盖屋的时候,要垫屋台子,就地取土,用铲车铲的。盖屋前,在距离宅基地30米开外的地方,挖下去将近半米,把屋台子垫高了半米,然后把屋盖在半米高的台子上。
我的那几间土屋位于村子的最西北角,向西、向北500米内,没有庄稼,除了盐碱地,就是茅草地,很开阔。北边有一个油田的加温站,算是我的近邻。
那些年,土地碱化严重,种庄稼靠天,雨水大,就涝了,雨水小,就旱了,风调雨顺的时候,庄稼才长得好。
我屋后的那片芦苇地,在低洼处,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春天,屋后的洼地里冒出一些草芽芽。到了夏季,阴雨连连,把那片洼地灌满了水,芦苇长得绿油油的,太阳一照,叶子上泛起亮光。时常看到鸟儿在里面栖息,水鸭子在里面觅食。那些芦苇,无忧无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绿了,枯了,又绿了,又枯了。
那些年,到了初冬,庄稼地里的活忙完了,母亲就拿上镰刀,去屋后割那些芦苇。
一割三四天。她弯着腰把割倒的芦苇捆绑起来,攒在一起。
过不了多久,有到村子来收购的,母亲就把那些芦苇卖了。几年之后,没有来乡下收购的了,母亲就让我弟弟用拖拉机拉到30里外的义和镇上,卖给加工苇箔的人家。那些芦苇,其实卖不了几个钱。但每年母亲都执意去割那些芦苇。
几年间,我几次劝说母亲,别割那些芦苇了。母亲说,那是我们家的,为啥不割?后来,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舍弃那一片芦苇。那三间土屋,是父母一块砖、一锨泥、一片瓦,辛辛苦苦给我盖的,有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有他们的憧憬和期待。土屋卖了,那些芦苇再没了,还有什么呢?
我在那三间土屋里结婚,两个女儿也在那里出生。那土屋,能遮风、能避雨,也能装得下日出日落、儿女情长。
2020年初冬,母亲得了重病,做了手术。出院不久,她一个人拿上镰刀,又一次把那些芦苇割倒,摊在了地上。
芦苇倒下了,母亲也倒下了。
后来,母亲走了,那些芦苇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一年年,孤独地生长,孤独地枯萎。
最后,那些芦苇,成了野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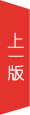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