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安
地理意义上的老家可大可小。
国人心目中的老家,大到整个国家,小到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在国外,外国人问中国人来自何方,答曰中国。在国内,有人问老家在哪,一般回答省市县,详细点说明乡镇村庄。
一次,儿子在惠灵顿机场遇到一个陌生人,他先用英语问儿子是哪国人,儿子用英语回答中国。他马上用中文问老家是哪里,儿子也改用中文介绍,老家山东沂水,生在青岛。他立即兴奋地说,原来是青岛老乡啊!并问,你爸爸做什么工作?儿子说在北海分局。当获悉我的名字他惊喜地说:“我是你爸爸多年前的同事,关系还不错。”同事卢景明旅居新西兰多年,他和夫人都是中国海洋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工作的。在异国他乡与国内老同事的儿子不期而遇,这可真是稀有的奇事。我也万万没想到,居然在新西兰的机场与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同事“间接”碰了个头。
我的祖籍位于沂河上游,跋山水库下方的东山村。我的祖辈因贫困迁徙到东山村以东二十里的牛岭村另立了门户。七八岁时的清明时节,我曾小跑步跟着本家哥哥们,去东山村外的祖坟添土烧香磕头祭祖。那时虽然对东山村曾是祖籍没什么概念,但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排解不了的感情。
我的档案履历里原籍填的是牛岭村,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老家,那里有我快乐的童年时光和年轻的日子。上大学后至今已近五十年了,其间一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衰老的人故去了,幼小的孩子长大了,小山村里许多人对于我早已陌生了,村里也早已“没有”了我这个人,但是在张姓家谱世系里,却永远写着我与后代的名字。我们没有忘了老家,老家也没有丢了我们。谢谢了,我的老家!
记得有一年,我带着一岁多点的儿子回老家,返程长途车在诸城郊区抛锚,司机钻到车下修了三四个小时也没弄好。只好跑到诸城县城打长途电话,叫来蒙阴运输公司的修车工,拆拆卸卸敲敲打打一直修到下午将近六点。长途车病病歪歪地开到青岛时已很晚,公交车不跑了。那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手机,我只好背着行李抱着孩子,艰难地走到离长途汽车站几里路的单位办公室凑合了一夜。妻子去长途汽车站没能接到人,问车站工作人员,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她担惊受怕地回到家中,整整一宿忐忑未眠。等天一亮我和儿子乘公交车赶回家,看到我们爷俩安全归来,儿子蹒跚跑着连声呼唤妈妈,妻子一把抱起儿子喜极而泣。那趟回老家让我一生难忘。
自从有了济青南线高速公路,缩短了回老家的距离,回老家的路已不像过去那么遥远。想回老家,儿子开车系上安全带,脚踩油门,拉着一家老少三代奔上环湾快速路,一会儿过黄岛,一会儿到胶州,过了诸城就是沂水。在车上和小孙女没完没了地说笑间,不知不觉两个半小时过去,车就停在老家门口了。现在不但交通改善,通讯也方便了,家家都有电话。逢年过节打电话和老家的亲朋好友互致问候,电话打回老家,心也就到了老家,心中便会油然升起回归的温馨与幸福感。
老家不讲条件地接受任何打道回府的人。而人们在疲于奔命、惊慌绝望之时,或功成名就、意气风发之时,也会自然而然想起老家。这种对老家的念想,是过眼烟云飘逝之后的一种情感归依。
虽然我的老家沂蒙山区至今还相对落后,但就好像子不嫌母丑一样,对生养自己的那方水土总觉得美不胜收。当见到打出沂蒙产地招牌的食品和农副产品,当欣赏到饶有风趣的乡村爱情电视连续剧,当看到每年千里迢迢回老家过年的在外务工滚滚人流。我突然觉得,“老家”这个原本内涵十分朴素的词语也变得生动时尚起来。
回想自己从故乡走向他乡,从山路走向马路,从少年走向老年,这一走,回故乡的路越来越远了,始终忘不了的还是老家。
江山易改,老家难移。任何人的老家都不能更改也无法代替,好像子女从母体自然带来的永远丢失不了的胎记。无论回不回老家,老家永远是祖祖辈辈改变不了的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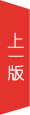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