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启昌
进了正月,村子中央那块空场地陆续热闹起来。拜过年、出过门儿的村人们大都乐意聚在这里,男女老幼一概穿着过年的新衣裳,高谈的高谈,阔论的阔论。小孩子好动,挣脱了娘亲的牵手,嬉闹着在大人们的眼前身后追来撵去。渐渐爬高的太阳则把暖融融的光照撒映在人们身上。
落在草苫和屋后背阴处的霜花消融时,村东跟村南两处路口相继有挑担的生意人进得村来。这些生意人衣着如上年腊月里一样,黑袄黑裤黑鞋帽,不过脸面上多了过年的笑容。叫卖的物品不再是腊月里的鱼肉鲜菜枣饽饽,而是一包一包大人孩子都喜欢的一拃多长的滴滴金儿。“买扎滴滴金儿,全家都欢喜儿。放花元宵节,天天心头恣儿。”搁稳挑担的生意人的叫卖声一响,村当央那块空场地上的村人们就格外活跃起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月朗星稀时放礼花,祖传的习俗。生活宽裕的、不怎么宽裕的,或多或少都会燃放一些,既是个仪式,也是个门面,当然也是种传承。很早时,村里有十几个潍坊来的知青,他们见过世面,跟村人说元宵节燃放的滴滴金儿实质是“火药引线”,或者叫“导火芯子”。南宋人周密曾在《武林旧事》中记载:每年元宵节,宋都临安要在皇宫中张灯结彩,其中“殿司所进屏风,外面钟馗捕鬼之类,而内藏药线,一燃而连响百余不绝。”药线,就是最早的火药芯子,也是最早的滴滴金儿。
滴滴金儿粗不过麦秸杆,长不过一拃有余,用一种格外簿的软灰色纸手工制成,上端留有一短截纸翼,便于燃放时粘贴或手拿,下端点燃后会随着“扑籁扑簌”的动静接二连三呲出一朵朵金色的火花,煞是好看。若是许多支滴滴金儿同时燃放,数不过来的金色火花连成一片,眼前呈现的便是阵势颇大且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色瀑布,令人激动亢奋。许是因了这些灿烂的情景,村人的元宵节才愈发充盈起叫人眷恋难忘的烟火气息,才叫人燃亮了对好日子的向往。
我家日子过得不算拮据,可是曾有近十个年头的元宵节没燃放滴滴金儿。为什么不放,我也没敢问。在我当兵头一年的正月里,父亲一反常态,老早买了若干扎滴滴金儿,声言元宵夜要在天井里的屋檐上、粮囤上、鸡舍上、葡萄架上,还有梨树上、百日红和月季花枝上全都贴上滴滴金儿。果然,元宵夜明月高挂,父亲、母亲,还有我和兄长分别手持香火依次点燃了父亲亲手粘贴的上百支滴滴金儿,诺大的院落里瞬间被“金色花朵”映照得通红,闻声而来的邻居和我们一家人身处“金色瀑布”之中倍感惬意。我侧目望向父亲时,一闪一闪的金花映照中,已过天命之年的他,眼眶里竟有泪水在晃动。
终于,父亲告知了近十年家里没燃放滴滴金儿而今重新燃放的原因。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文化底子薄,但他有毅力,刚成年便当上脱产医生,在外悬壶济世。不料,因一桩错案被解去公职遣返回老家。父亲心有不甘,凭技术在村里继续为街坊把脉诊病。将近十年后,父亲终得平反,恢复原职。高兴呀!
在部队时,有年正月十五夜正值我站岗,望着不远处几个村镇不时闪烁起的滴滴金儿的亮光,脑海里随即浮现出老家庭院中父亲领着一家老小燃放滴滴金儿的情景,那情景清晰而又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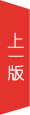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