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占
如果以青岛城市标志栈桥为圆心,有一天我猛然发觉,这半生都没能走出其方圆三公里。我看过世界,珠三角、闽三角、长三角都有我多年求学务工的轨迹,亦有前男友散落其中不相往来。我真的看过世界,世界上最著名的四大艺术博物馆都去过——还不止一次。卢浮宫在巴黎塞纳河北岸、大英在伦敦新牛津大街、大都会在纽约第五大道、艾尔米塔什在圣彼得堡涅瓦河畔。除此之外,我在希腊小岛也呆过一阵子,就是诗人歌手老科恩上世纪六十年代呆过多年的伊兹拉岛,他在那里写下了经典中的经典《美丽的失败者》。岛上没有交通工具,我通常步行,偶尔骑驴,绕着神秘的马蹄形海港,在蓝白相间的房子之间,或热牛奶一般倾倒而下的阳光里,怀念他。
还有很多独特之地,在此不一一赘述了。总之我还是回到了青岛老城,回到了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父亲的出生地,沉潜下来,写写画画,安身立命。从精神层面讲,老城是文学的母题和原乡;从物质层面讲,老城是我闭着眼也不会迷路的地方。出门向左,走上二十几步的马牙石路,然后往右,下七级石阶,直行。紧接着,一段大于45度的上坡和一段小于30度的下坡让身体前倾后斜。再次直行,再次遇到石阶和更多的锐角。最后,穿过十字路口,便可见海,海潮已经退到了底线,栈桥近在眼前。
老城的路都是沿海的路。一百多年前,青岛的先民们在繁衍迁徙的过程中踩出了路的雏形,它们承载起生活的重量,成为通往海边的过渡、干道或分支,参与了城市生活以后,叫做街道。是那些波浪般起伏的街道主宰着老城的走势,折叠,起伏。街道有主次,宽绰一些的通常与海岸平行,条条衔接着,一直向往东边的新城。蛇行的分支早已变成了凋敝的小巷,慌乱的石板,丝绒样的苔藓,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巷子一边,伸手可及,让人不得不替窗户里的秘密和安全担心。主街当然不同,即使旧了,也底气十足。更何况,主街从来不会真正地旧掉,在沧桑的背景上,时尚一茬茬地生长着,长大后就扑棱开巨大翅膀,不知疲惫地在城市里求证嬗变。事实上,时尚也是有基因的,比如,一个世纪以前的咖啡馆、红舞厅、俱乐部……千回百转之后,又在老地方经营起相同的生意,今天的场面因为昨天的传说而鲜艳,而浓烈。
有时候我躲在书房里,枯坐于电脑前,夜深了人们都散了才肯出门跑步。有时候天堪堪放亮,我第一个冲进早集市买回当日所需食材,就再也不出门了。更多时候,我无法摆脱对于街头的迷恋。海边的路,云上的路,终究都是心中的路。方圆三公里,抬腿就走的感觉真好——不用转来转去找地方停车,不用操心是不是单行线,不怕塞车,不必路怒,更不要付汽油费。这种时候,我会爱上行走,甚至想,如果能一直沿着海走,我愿意走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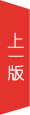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