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
经过长途颠簸,我下了车。映入眼帘的是饱经风霜洗礼早已斑驳不堪的村名石:“嗨,好久不见。”
远处,从村里一路小跑着来了一个人,边跑边挥舞手臂,用浓重的乡音唤着我的小名,似曾相识的红头巾在这冷风萧瑟的季节十分扎眼。她是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小时候跟妈妈回老家,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她带我放羊、粘知了。她年纪轻轻就干农活扛起重担。
“来了?”她满是老茧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来了。”我微微一笑,手却悄悄往回缩。“走,回家暖和暖和。”她像没察觉到,很自然地接过行李,拍拍我的背,领我向村子里走去。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路还是土路,这么多年竟一直未变。脚下的碎石子和鞋底相互摩擦咯吱作响,在冷寂的傍晚充斥双耳。这让在城市待久了的我有些不可思议:“还没修路?”她叹了口气:“村里总说没钱,哪像城里的大路,宽敞又干净。”我嘴上说着“没什么”,心里却为“城里人”的身份沾沾自喜。
路两边的土地光秃秃的,全然不见一丝绿色,只剩黄土与觅食的麻雀相伴。见我沉默地望向田野若有所思,她笑着说:“还记着那年春天你来,指着满地的麦子问我‘怎么这么多的韭菜’。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你都比我高了。你学习也忙,这些事儿估计你都忘了。”她不住地感叹着,没表达分毫的遗憾,我却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到落寞与无奈。
一路上她指着不同的房子,告诉我这一家的姐姐小时候一起捉过蝴蝶,那一家的小弟打弹弓特别准。在田野上放肆地奔跑追逐,累了就躺在地上,一扭头鼻边就有小花芬芳,往事好像就在眼前。我的心情有些许复杂,只是微笑着点头,跟在后面默默地走。
来到熟悉的房子前,大门院井,一切如旧。院子里一大盆小山般的衣服还飘着泡沫,大概是刚洗了一半,怪不得她身上有大片水渍。“不用洗衣机吗?”我问,她淡然一笑:“手洗干净,习惯就好。”就像说着别人的事。我望向她操劳已久的双手,不知结了几层厚厚的茧,看不出纹络皱褶,全然不似女孩的纤纤玉手。想到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都是父母一手包办,这巨大的反差让我的心禁不住颤动起来。
十年,她身上的生活重担越压越重,独自忍受着贫困,却依然坚强勇敢乐观。而我,却在虚伪乏味的城市里越陷越深无处藏匿。
进了屋子,一股暖意扑面而来,柴火烧得很旺,那是不同于空调吹出的暖风的踏实温暖。不大的房间,家具摆设质朴洁净,最值钱的木质沙发在岁月的沉淀中更显古朴。安置好行李,她麻利地倒了杯水递给我。一口饮尽,我咂了咂嘴,那是独属于井水的甘甜。
问了问家中的近况,她眨眨眼,叹口气道:“城里就是不一样,不比我们这地方,又脏又穷,出去的谁也不愿意回来。”说着头就无力地低了下去。安慰的话我无从说起,因为十年未曾来过的原因我自己都觉得幼稚可笑,怕她听后会更加难受。是啊,已经十年了。你知道吗,我没有忘记。时间会把坚硬的巨石销蚀成细沙,但仍有些美好记忆经得起碾压磨损,藏在海底深处依旧光鲜亮丽。而这些,我费了十年才彻底清楚。
本来约好一到农闲就回来找她,去爬山去采野花。可我无法忘记,当我兴致勃勃地提起这些我认为最难得的快乐时,朋友们嘲笑、不屑一顾的眼神。于是,为了“自尊”和“好友”,我渐渐刻意迎合她们,对“原始”的乐趣嗤之以鼻。每年,在电话里我总是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到后来,她再也没打来电话。
十年,最终站在这片土地上我才知道,自己耗费了太长时间去感知,什么样的快乐如霓虹灯短暂闪烁,什么样的美好似钻石光芒永恒。
离别时刻,她站在路旁目送我上车。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那时哭得稀里哗啦,被强拉硬拽离开村子的我。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却已有十年之久。车子启动,把不停挥手大声喊着“有空常回家”的她远远甩在后面。渐行渐远,只能依稀看到红头巾越变越小。
十年,的确太久,让你孤单太久,让我虚伪太久。人生路长,我会伴你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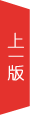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