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义瑞
一辆崭新的黑色红旗牌轿车停在街门前。
左邻右舍的人们兴高采烈地围观着,讨论着。这是我家买回的第二辆轿车了。买第一辆是在十多年前,儿子在城西工厂上班,儿媳在城东工厂上班,一东一西相距三十多里,不是他送她,就是她送他,逢上阴雨天或哪个有事,一辆车就打不过点来了。经过他们二三年的努力,我把和老伴侍弄几亩地得来的钱也凑上,又买了这辆新车。这回,儿子跟儿媳妇上班下班就方便多了。
儿子儿媳喜笑颜开地从家里走出来要去试车,我却退回院子,躲在一角抹起眼泪,因为想起四十多年前母亲坐车的往事。
那是生产队时期,我的姥娘家在即墨城北阁里,那些年母亲常为我们兄妹六人上学、吃穿、盖房、婚姻等杂事专程回一趟姥娘家。父亲为多挣工分没工夫,所以,母亲往返姥娘家都是由我用木棚独轮车推着,所用的木棚独轮车一般都是在队上收工后或者不用时借用的。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母亲又要回姥娘家,还是我去送她,父亲早早地去队上借回了独轮车放在门口。为了母亲坐在上面安稳舒适,父亲把车棚右边绑上一个草把,垫上麻袋和被子。我支起车,六十多岁的母亲坐到了车的右面,父亲把提前准备好用来保持平衡的石头搬到左面,我便推着母亲上路了。
青沙路穿过我们村子,沿着公路向前走了约莫三里路,到了一个高坡前,我把套在肩上的车襻往车上挽紧一道扣子,又往左手和右手上各吐了一口唾沫,弯下腰,憋足劲,只想一股劲爬过高坡去。车子刚前行了不多远,谁知坐在车棚右边的母亲,两手紧紧抓住车棚中间的高架,突然间一个起身,从坐在车棚的草把后面坐到了前面,并狠劲地往前弯腰,嘴里还说:“帮着俺儿使点劲吧。”此时,我深深懂得母亲的想法,她以为这个办法能够减轻我的劳苦,可母亲哪里知道,车头左边那块保持平衡的石头重心在前面,母亲把身子向前一倾斜,整个独轮车的重心全部转移到前头了。当年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个子瘦小,平时又没经过锻炼,可真有点支持不住了,既要使劲向后按住失去平衡的车把,又要使劲向前推着。我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硬是向坡上慢慢爬着。如果我说了这样一来更费劲,母亲明白过来,她心里又会难受一阵子。我头上的汗,流到嘴里又咸又涩,淌进眼里煞得睁不开眼。我只得不断地摇着头,将汗水往四下甩开。千忍万忍,一步一步前行,终于爬过了高坡下了坡,我把独轮车停在公路右侧,母亲重又在车上坐回草把的后面。我喘了几口粗气,像落汤鸡似的疲乏地站在独轮车后,依然十分关注着母亲和车的平稳。母亲转过脸关切地对我念叨:“尽是处置俺儿啊。”我知道这是母亲心疼我的一句话。
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正碰上村里有一辆拖拉机去城里供销社拉化肥,经过姥娘家门前时,见母亲在街门口站着,开拖拉机的张叔叔停下来和母亲打了个招呼。母亲向人家说了自己想搭车回村,张叔叔就把母亲顺便接回来了。那是母亲第一次坐拖拉机,一进家门她就满怀感激地对我们说:“要是有事往哪走走都能有个拖拉机拉着,多快多好。”这话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我却牢牢记在心里。
苦尽甘来,如今我家已有了两辆轿车,但母亲没有坐过一次。每当和家人一同坐上儿子儿媳的轿车,我总会想起母亲坐拖拉机那溢于言表的幸福神色。坐上轿车我会感觉母亲在我身边,真想让已去另一个世界的她享受这新时代的欢乐与幸福,以弥补我终生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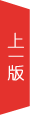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