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璐
身处现代生活中,或许“炉”只会让人联想起“炉包”“炉鱼”“挂炉烤鸭”。我仿佛也即将忘记这个字,忘记那烧得通红的三圈炉盖、烤出油的香甜地瓜、咕噜冒泡的大骨汤……忘记是它,温暖了我整个童年的冬天。
上小学时,我就会生炉子了。那年,学校刚落成。夏日里看起来宽大的教室,到了深冬,却显得萧瑟、寒气逼人。还好,教室里有炉子,一只砖红色铸铁、胖胖的炉子。每日清晨,我第一个来到教室,开始与炉的对话。
炉膛里,还残留着前一天燃尽的煤灰。清理之前,得稍加点水,让炉盖露出一条小缝儿,火钩刚好伸进去。搅动一番,听话的炉灰便落了下去;也总有不听话的,要从下面的炉门伸进去掏一掏。炉灰全部落入灰斗,炉膛算是清理好了。此时的炉,虽然干净,却空洞、冰冷。
准备生火了。火柴、报纸、木头、煤,小小的我麻利地备好物料、手起刀落、一气呵成。
报纸要团成“球”,点燃后迅速放到炉膛里,顺势加入大小均匀的小木块。很快就可以听到噼里啪啦的细小声响,闻到燃烧的木香了。加煤是“生炉子”的核心环节。刚刚燃起来的木头能否把煤点燃,取决于煤的品质、数量,也取决于加煤的时机。如果运气好,煤里恰好有稍大的“煤块”,这时就派上用场啦;如若不然,便要把少量的、掺水较少的煤,轻轻地、松散地覆盖到燃着的木头上。第一波煤燃起来,基本就大功告成了。砖红色的、胖胖的炉,热乎起来。
炉越烧越旺,同学们陆续来到教室。教室里热闹起来,因为炉,也因为一张张天真的笑脸。我在那时真切地感受到“助人之乐”,在心里埋下一颗多行善举的种子。没有人可以天然拥有某项技能,我的这个本领当然源于他。虽然,我并不记得他专门给我上过“如何生炉子”的课程,可是“置办炉子”这项入冬仪式,应该是我永久记忆的一部分了。
炉子和烟囱都是前一年用完之后,敲打、清理、仔细收纳起来的,可以直接拿来用。炉子比较好对付,固定好位置就行,接烟囱可是个技术活儿。把裹烟囱的报纸一层一层拨开,露出一节节、泛着金属光泽、有雪花图案的烟囱。按照设计好的路线,先在地上排列好顺序,找准“大小头”,拐脖、直筒、直筒、拐脖……精准对接成三维立体的烟囱组合。就靠它,连接起炉子和烟道。
接下来,我负责扶好立着的烟囱,他踩上板凳,用一根细不可见的铁丝加固,然后跳下板凳,在我扶着的位置轻轻一晃。纹丝不动!我们笑了,他低头看着我,我仰头望向他。顺着这个通道,温暖流动起来。
那时候的冬天不怎么好过,天寒地冻、物资匮乏。可是,从支起炉子的那天开始,日子便开始有了颜色。放学时推门而入,暖流扑面而来。扔下书包,一屁股坐上小马扎,两只手在烧得通红的三圈炉盖上方不停地搓。炉盖最外圈,经常放着几只地瓜,皮已经皱皱巴巴,油从浅浅的沟壑里流出来。偶尔也会是几片馒头,烤得脆脆的,格外香。最幸福的,还是喝大骨汤的周末。一只大海锅里面装上大棒骨,在炉子上煨上大半天。傍晚,我被安排去南边的豆腐社买豆腐,再去西边的粮店买“杠子头”。“杠子头”是一种硬面火烧,外面烤得焦黄、里面层层分明,散发着浓浓的粮食香气,让人感到心安。一家人、一锅汤,幸福可以很简单。
生炉子的日子里,入睡前他会小心地把炉子“培”好,然后走到我的小床边,帮我塞紧被角,“睡吧,爸爸在家呢。”
您在初夏时离我而去,我在四季里寻找您的影子。谢谢您留下的讯息,让我在寒风乍起的日子里,有了可以想念的人。深夜独行后,那只“炉”可以温暖我,一如当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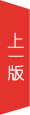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