邴 琴
天空先透出不一样的蓝,给风起了个头。野草们从早春开始生长起来。他们将细细的枝节、扁圆或狭长的叶子拼命覆满盆口,不停往外延伸,牢牢地将土壤扎牢。风掠过的地方散播下绿色,马唐、荠菜、苦菜、云青、牛筋草、马齿苋、鸡肠草、路边青从干黄的土里翻滚出来。
土壤里埋藏着各式野草种子,像是宽厚的母亲天然孕生出来的,一夜之间便随风刮出一片波涛。
城市里没有土壤铺张的空间,如果不想失去对植物的体验,只能将所有的花草树木栽植进花盆里。于是,我将秋天留下的种子覆盖在春天的土壤上。我总幻想可以模拟每一棵植物所需要的深度和宽度,每一个花盆都安排得足够大,让植物的根系不必蜷缩起来自我改造。上个深冬六十年一遇的极寒天气,冻死了院子里的两棵桂花、两棵石榴、两棵无花果、三棵月季。空出来的花盆荒在那里,我还没有丈量好该栽种什么新鲜的植物。
等我开始留意的时候,野草们已经兴旺旺地长出来了。那么蓬勃,那么张狂,那么肆意。他们野生野长,芜杂中颇有抑扬顿挫之致。他们天然知道应该怎样安排那些枝枝叶叶,他们有独特的结构次序,有延展的主线,有渲染烘托得整齐中的变化。这使马唐的节节叶叶如风中之竹楚楚动人,使丝路蓟那样的硬汉更加挺直了叶缘上的锋刺。这是朴实生命力的美学谱系,莫可名状,实实在在存在。于是,那些荒着的花盆,以自由崭新的姿态,让我的院子有了一番簇新的意味。
分不清楚,这些野草是依靠风力吹到了我的小院,还是土里本身带着野草的种子。这些天生地养的野草野菜,滋溜溜地往上冒带着质朴的清气和天然的甘香。
当我开始留意起院落里的野草时,我意外地发现了灰灰菜、车前草、蒲公英、苦菜、云青、马齿苋这些曾经无数次滋养过我成长期的胃口、给予我乡愁滋味的野菜。于是,我决定用记忆里母亲的手法做出关于野菜的一桌鲜。
云青和马齿苋,大多数做野菜的人都会将其分别做成两盘菜。我却沿用了母亲的理由与传统。母亲说云青口感干硬,而马齿苋滑溜溜润喉,两种野菜被热水焯过、再经凉水拔过之后,切成1厘米小段,以五五比例配以蒜泥凉拌,吃下去的才是相互融合,互相激发出真正春天的味道、来自泥土的芳香,谓之“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等到深秋过后,干枯的野菜也会被我拔除集中起来。那些我随手清理过的野草,用塑料袋扎起来密封,放在半阴半阳的地方大约1个月,就可以得到天然有机的植物肥料。这些肥料,可以使逐渐硬实的土地复归疏松肥沃。这些泥土,又将生长出新的花草与野草。
从历史深处拱出的野草,在晚风中无数次轻轻摇晃,野草比我们更持久地置身于时间之中,以一种更加简洁的方式诠释着生命与生命力的双重命题。此时此刻,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肥沃、繁华、跳跃、安宁,土地孕养出欢欣生长的野草,野草以被收割的方式补充着另外的生命形式或者重新回归土地。
没有什么比野草对大地更忠实,这是委于大地的泥土中无法被夺取的生命。那些荒盆从来没有真正地荒过,未来的四季将属于另一个新的生命。每一个清晨与黄昏,风在摇她的叶子,一些看不见的种子一枯一岁地留了下来。掩盖着野草种子的那片土地,将再次发芽、生长、开花、结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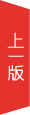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