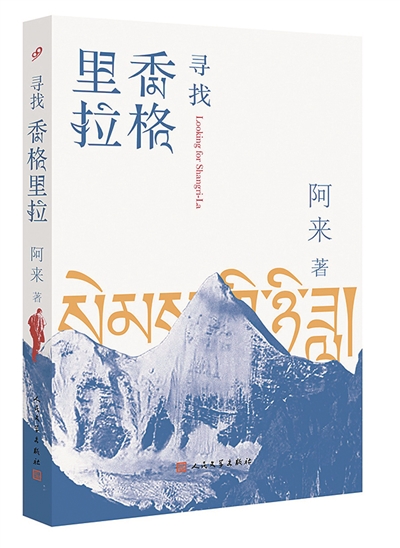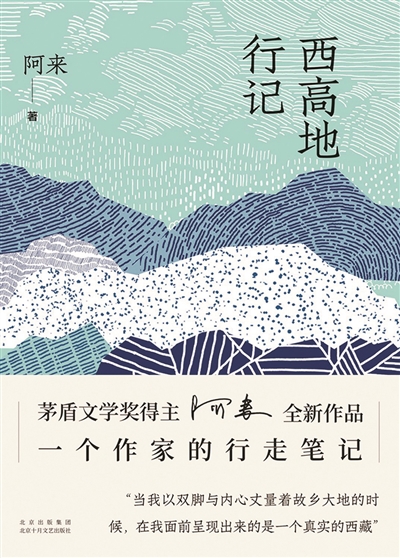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整个八月,作家阿来都忙于在三种不同的文体间转换,漫行于他熟悉的雪山沃野,或溯源“植物猎人”的源流,或仰观苍穹,或凝神草木生灵——
行走笔记《西高地行记》,界于小说和剧本之间的《寻找香格里拉》,诗集《从梭磨河出发》——2023年下半年面世的三本新书同时亮相上海书展,让阿来成为八月图书活动中最活跃的作家,也让人们得见这位以藏地独特人文描摹和史诗化吟咏见长的书写者,在大地行走间的另一番生命遐思。
二十三年前凭借一部《尘埃落定》声名鹊起并斩获茅奖的阿来,今夏出现在一档名为《我在岛屿读书》的综艺节目中,因为曾经书写了“山珍三部”《河上柏影》《三只虫草》和《蘑菇圈》,对各类植物如数家珍的他在节目中被称作“植物学家”。对于植物、对于自然的痴迷与热爱也浸润在阿来的新作中:《寻找香格里拉》钩沉一百年前的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在中国持续27年的探险传奇,跟随洛克这位充满野心的历史人物,我们得以深入传说中的秘境,看见不一样的山野风土;《西高地行记》中,一幕幕高原自然景致,是作家与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等万物交汇的步履;而在《从梭磨河出发》这本诗集里,自然地理将读者引向作家的文学创作原点,与更丰盛的精神世界相遇……
作家莫言惊叹于阿来对植物的了解,他写过一首诗,开头便是“欲知草木问阿来”。评论家李敬泽也称赞:“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不过这种凝视和珍惜并非拘泥于笔端的想象,而是得益于广阔行走的经验。而行走中的阿来,也并非只为了抵达地理意义的远方。他说,要认真地像一个作家一样生活,对于一个地方的了解,有没有掌握关于那地方的文学和诗歌的书写,有巨大差别。据说有一次去南美,他就拒绝了统一安排的观光路线,坚持只去聂鲁达的故乡,因为唯有了解过他的诗歌与生平,旅行才具有意义。他始终坚持认为:“文学才是旅行的目的地”,在抵达地理上的远方的同时,更要抵达思想和审美的远方。
行走也带给阿来深邃的思考动力,在《西高地行记》中,他写道:“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
不完美的“植物猎人”,复杂性正是他吸引人的特质
40岁就以《尘埃落定》斩获茅盾文学奖,成为最年轻茅奖得主的阿来,曾发誓“一辈子不碰电影”,甚至婉拒了为《尘埃落定》做编剧。没想到后来却因缘际会三度“触电”。第一次是为2014年的电影《西藏天空》做编剧,讲述上世纪50年代藏地男女的精神解放;第二次是写2019年的电影《攀登者》的剧本,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故事;缘起于一部夭折电影的《寻找香格里拉》,是阿来剧本小说的第三番,讲述一位一百年前的“植物猎人”在中国西南大地行走的传奇经历。
如果将此三部不同时间线的创作类比,就会发现,它们都具有史诗般的藏地氛围和对自然世界充满感染力的荡涤灵魂的描绘,并共同抱持对所在世界的极限探索精神。这似乎也是阿来文学创作一以贯之的主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探险家、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作为美国农业部特派专家、国家地理学会考察队队长来到中国,他先后在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采集植物种子、标本,拍摄照片,历尽艰险进行科考探险,深入到传说中的世外胜地“木里”,作为第一个抵达此地的外国人,他发现了贡嘎日松贡布三神山,并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他的发现,世人由此知道了“香格里拉”。作家阿来花了12年时间,三进“木里”,追寻洛克的脚步。
青报读书:您所写的《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蘑菇圈》,被誉为“山珍三部”。在《我在岛屿读书》那档读书节目中,您对各种植物如数家珍,这本讲述“植物猎人”传奇故事的书,创作动机是否正缘于对于植物以及自然的一种特别的偏好?
阿来:是的。2006年我曾有机会去唐古拉山、可可西里,正是5月份春天刚刚到来,残雪消融,有一天忽然发现花就在雪地里边开了。现在我知道这个花叫报春,雪还掩着一半,这么顽强又美丽的生命!这时候我发现自身有巨大的缺陷,也是有些中国人的缺陷——不关心环境。我们不认识身边那些跟我们一样美丽的生物。所以我从那时开始系统地学习植物学。因为有了这个爱好,我开始关注一类人物,就是到中国来的外国探险家。
清末民初,很多外国探险家到中国进行探险,他们中有的进行地理考古,有的在中国西南地区研究生物的多样性。这种故事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当西方人来到那个时候的中国,他们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优越感;另一个方面,他们研究动植物确实有眼光。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内心会很矛盾,一方面对他们的科学精神很欣赏,但另外一方面又对他们那种殖民心态很愤怒。
青报读书:主人公洛克,在小说中既是一个执着的冒险家,又是一个追逐名利的野心家。在他身上,有什么特别吸引您的特质?
阿来:洛克执着科学探险,对所有文化现象都有深度兴趣的学者素养是令人非常敬佩的。他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他的父亲是贵族管家出身。所以他小时候就养成了一种有点分裂的性格,生活优渥又不是贵族,一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贵族”。后来去了美国也非常努力,他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但在夏威夷大学成了一名植物学家。今天在夏威夷,很多植物最初的命名都是由他完成的。
他希望他的植物学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后来就得到一个机会:美国农业部要招募一个人,具有探险精神,有非常好的身体,同时也要懂得植物学,到中国来广泛收集动植物的标本和种子,所以他就在上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长期住在云南丽江。因为这里是横断山区南端,中国生物多样性物种最丰富的地方。这个人非常下功夫,他的摄影技艺也很好,《寻找香格里拉》封面用的就是他拍摄的央迈勇雪山的照片。
来到中国,他有很多“野心”。后来在哈佛大学的植物园里还有他移植自中国的植物,哈佛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他的日记,以及在此期间拍摄的照片,夏威夷图书馆有相当多的中国植物标本。
但是“野心”并未掩盖他在动植物学领域的成就,尤其是他对丽江居住地的纳西族文化的贡献——一本大书《中国西南的古代纳西王国》,可以看作是研究该领域的权威著作,同时,他还编译了纳西文和英文的《双语词典》。
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面对事情贪婪、骄横、自私又冷漠,同时又要展示自己的能力,扬名立万,而把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历史人物展现出来,才是一个足够丰满的人物,对于今天才具有意义。
青报读书:《寻找香格里拉》的每一章节都极其短小精悍,如一帧帧画面显现,而且所有的章节都以地点命名,有的章节甚至不足百字。为什么会采用如此轻量级的文本塑造人物,展开叙事?
阿来:这本书的文体有点新颖,因为它介于剧本和小说之间,所以读者读到的东西更具有镜头感,甚至有旁白的出现等等。正因为如此,所以读起来有点不像小说,在写作文体上是一种创新。这是因为《寻找香格里拉》本来是为电影写的,是根据真实人物事迹所写的电影文学作品,当时决定要投资这部电影的投资方不投资了,所以成就了现在这本书。电影没有出生就让它“胎死腹中”,原本想想算了,但是架不住出版社的朋友鼓动,还是出版了。
青报读书:书中那位名叫埃德加·迈克的美国记者,在故事接近尾声时成为一本封面印有中国士兵吹号剪影的书的作者,暗合了现实中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洛克说,“他找到了他要找的革命军队。”……读到这里,突然有一些动容。
阿来:斯诺这个人在中国比洛克有名多了,那个时候是作为《太阳报》刚出道的记者到中国来冒险。这两个人谁也看不上谁,斯诺不因为你带着我、罩着我就要听你的,这也是他身上显得可爱的地方。他首先看不上洛克高高在上,对下面中国人的一种态度,洛克也看不惯斯诺,认为他同情了不该同情的人。最后二人在半路分道扬镳,结果几年后斯诺最终去了延安,才有了《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书。
青报读书:您是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之前《瞻对》就是关于大历史的非虚构写作的范本,而这次《寻找香格里拉》的故事在轻盈的背后,是否也有着没有讲出来的真实历史?
阿来:历史永远不可能如此简单单一。不要小看了“植物猎人”,今天遍布世界的茶叶就是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从武夷山偷走的,偷走的远不止一棵树,而是整船整船茶叶运到印度去种,还要带上全套工具、匠人(从种茶到炒茶),最终把中国的福建茶在阿萨姆引种成功。今天全中国所有茶叶产量加起来不如英国的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就是印度的阿萨姆,所以,这也是一种资源,过去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全然没有认知……
我们从文学创作当中可以看到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从而也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何去何从作出反思。
青报读书:特别喜欢您之前的一句话:要认真地像一个作家一样生活,把书本的阅读学习,大地上、人群中的行走都作为积累。这又让我联想到您在上海书展上所说的文学的功用,它是用来感知世界的。
阿来:最近我又去了一次亚丁,从成都坐飞机35分钟就降落了。他们现在建成了一个景区,即将在国庆前开放一个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方面的博物馆,我也去做义工帮他们做一些博物馆展陈以及文字方面的工作。这次又把洛克露营的地方走了一遍。1928年他走过的路线、去过的地方、他当时所看见的,所拍摄的地方,在今天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我想要感知的。我来倾听,来感触,来思考,来证实,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或许今天仍在某处上演。
一本精微的植物笔记,如何将风景写好
阿来的最新散文集、行走笔记《西高地行记》,收录了他于2011年之后创作的9篇长散文。包括《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平武记》《玉树记》《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记》。
阿来表示散文有两种编辑方式,一是编年,二是统一在某个题目之下,例如他的《成都物候记》《西高地行记》,既是植物笔记,也是美学笔记、文化笔记。《西高地行记》收录的散文有一个统一的地理环境,就是以青藏高原为主的西部高原地。
在日前的一场读书活动中,作家卢一萍评价阿来,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学矿藏、拓展文学空间,宏大到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精微至《故乡春天记》里对两种蓝色鸢尾的观察和区分。他说,如同他曾经创作的《大地的阶梯》,《西高地行记》也有一种在温暖、悲悯之上的“神圣视觉”,马尔康、嘉绒、贡嘎、平武、玉树、果洛、山南、武威、丽江,构成了一个仰望视角的高地。
在《果洛记》的开篇,显然是坐在车中的阿来描绘了他所看到的:“高原上一切的景物:丘岗、草滩、荒漠、湖泊、沼泽、溪流和大河,好像不是汇聚而来,而是在往低下去的周围四散奔逃……风景从身边一掠而过:缓缓起伏的丘岗,曲折萦回的溪流,星星点点的湖沼,四散开去的草滩,还有牧人,和他们的帐幕,和他们的牛羊……再然后,那些风景在身后渐渐远去,闭合,滑落到天际线下。”如何将风景写好?他给出了答案,“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不是给草原加上‘美丽’‘宽阔’‘碧绿’的定语,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它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徒步、骑马、坐直升机时看到的,而是一种快速前进、绵绵不绝、一晃而过的视觉,在你的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同时,他还提出,“写作时的书写对象是体积。当它的尺度、口径不一样时,着力的笔墨就不一样,所以有些粗放是必要的。”犹如写意。
《西高地行记》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三个向度,分别对应地质学、文化学、动植物学的知识储备。有了这三个向度,文章才变得立体起来。
回到文学的原点,把写作带向更广义的诗
“诗歌可以被看成阿来的阑尾,阑尾其实包括了身上所有的干细胞,是基因库。阿来的诗歌包含着他所有的文学基因。阿来的诗歌、散文、小说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基因。”新诗集《从梭磨河出发》在上海书展亮相时,熟悉他的朋友黄德海从批评家的角度出发指出他与诗歌的关系。诗歌是阿来文学创作的起点,似乎也决定着他所有文学创作的样貌。当他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就开始了高原上的诗意漫游。这样的经验也让他之后的小说文本散发出诗意的气质,《尘埃落定》中的语言就以其深具诗意之美为读者称道。
在30岁时,阿来的写作从诗歌转向了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尘埃落定》。提及自己从诗歌写作转向小说的起因,阿来回答:“我的诗歌其实是一个游戏,但我没想到这个游戏把我带到了一个严肃的世界,那就是文学。我们年轻时在摸索不同的方向,这也是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当时,写诗的时候我也在写中短篇小说。1989年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诗集《梭磨河》,我就是喝梭磨河的水长大的,我就在那片有雪山、草地、森林的地方长大,这个地方也是我的出发点;另一本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但我那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作家?我认为我和这片土地和自然有一种互相感知的关系,因此决定这辈子要严肃对待文学。
《从梭磨河出发》收录了包括《风暴远去》《这时是夜》《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灵魂之舞》等风格鲜明,意象高雅的作品。这些诗歌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流畅的叙事展现了辽阔寂静的高原生活,以质朴真挚的笔触抒发阿来对祖祖辈辈世代生活的土壤以及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在这本诗集的后记中,他提到了聂鲁达和惠特曼,还有他所钟爱的音乐家贝多芬,他说,他感谢伟大的诗人,感谢音乐,“不然的话,有我这样生活经历的人,是容易在即将开始的文学尝试中自怜自艾,哭天抹泪,怨天尤人的。中国文学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有了两位诗人的引领,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
即使已经停止了诗歌写作,但阿来的诗情并未泯灭,他只是将诗情转移了。阿来直言:“这些诗永远都是我深感骄傲的开始,而且,我向自己保证,这个开始将永远继续,直到我生命的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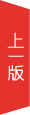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