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
四十余载的光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于这片土地却是沧海桑田。我每日穿梭于城市地铁公交中,习以为常地看着街市如织的车流,霓虹闪烁处,尽是人间繁华。
前几日回到故乡的老房子,院墙早已破败,院里杂草丛生,墙上斑驳的老相框内,儿时在雪地里和姐姐一起成长的身影仍留在黑白照片里。多年没见的老邻居用浓重的乡音说,现在生活真是好了,餐桌上的花样多了,身上的衣着光鲜了,出行的方式快捷了,又说谁家老人走了,谁家房子也空下来了。我看着他,想着他年轻时的模样,不知道怎么回答。经济腾飞的速度,快得让几代人的记忆都追赶不上,那么我和他们的内心能跟得上吗?
人非机器,不可能说升级便升级。我常见地铁里的人们眉宇间锁着难以名状的焦虑。他们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目光却涣散如雾。各行各业效率之高,早已超越“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梦想,但心灵的安顿,反倒成了难解的题。
人终究不是简单的生产工具,会哭会笑,会痛会梦,需要一些精神寄托,需要做些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不太聪明”甚至“愚蠢”的事。这正是人人各不相同的区分所在。
想起苏轼在《临江仙》中的吟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九百年前的叹息,今日听来依然真切。这位屡遭贬谪之人,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反而找到了心灵的归处——“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在黄州垦荒种田,在惠州酿酒,在儋州办学,世人眼中的“苦难”,却成了他安顿灵魂的契机。
江南某镇,有老鞋匠守着一爿小店,手工制鞋,每双需旬日。游人常惑:“机器生产,片刻即成,何苦费时若此?”老匠人微笑不答,只将手中皮料细细打磨。试穿其鞋者,皆言舒适异常,如踏云絮。原来他每遇客至,必先观其行姿,与之闲谈,察其性情,量脚定制。这哪里只是做鞋,分明是给奔波的双脚找一个安顿处,更是为浮躁的心灵寻一处栖息地。
如此看来,种种“不智之举”,实则是为灵魂寻找安处的努力。高楼广厦让人得以栖身,而心灵之所却需另觅归处。正如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艺术的慰藉》中所说:“艺术不啻为一种治疗方式,帮助引导、告诫和抚慰它的受众,协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那些看似“不太聪明”的艺术活动、手工制作、田园劳作,实则都是对灵魂的治愈,是对异化生活的抵抗。这归处,或许在方寸阳台的花草间,或许在深夜书房的灯影下,或许在老友对坐的茶香里。
记得《菜根谭》中有言:“闲中不放过,忙处有受用。”古人早已参透忙闲之道的奥秘。今人每以“内卷”自嘲,而不知所以卷者,正是将全部生命价值系于外在成就之故。若能在功业之外,另辟一方心灵田园,或可免于无限竞逐之苦。
今年天气格外炎热,上周终降一场大雨。我正在阳台上收衣服,瞬间雷声大作,暴雨倾盆。闻着雨冲洗着树叶的清香,我决定放下琐事,拿一板凳坐下,静静听着急促的雨声,忽然明白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中所说:“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不妨放下手机,静坐片刻,听一听内心的声音。那里有一个家,永远为我们敞开大门,等待漂泊已久的灵魂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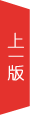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