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寒儿
相比于描绘大自然间的花草,张朋先生描绘瓶花和盆花的画作虽略显少,但这部分作品里的传统日常元素,往往弥漫了一种淡淡的人间烟火气,亲切可感。与此同时,张朋先生笔下的器物之美,彰显了“朴、清、厚、率”之风,是他诗意美学的最佳诠释。
张朋先生在瓶花与盆花的创作中,也格外注意岁朝清供、寿诞清供等不同节日的时令习俗。在《富贵平安》中,真国色的牡丹绚烂盛放,画面中不仅有三个红彤彤的鞭炮,花瓶上还盘了一条龙。除了龙,张朋先生还在瓶花的瓶身上绘制过鱼等图案,中国远古图腾和传统民俗元素的组合,物华天宝,富贵雍容,处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从《百事皆好》《富贵平安》和《春风长在画人家》等根据题跋而来的名称也不难看出,这一类作品承载了张朋先生真挚的期盼与美好的祝愿。
在中国传统民俗中,人们喜欢用谐音字和同义词来传情达意,这一点在张朋先生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尧年千万寿》盆栽中是万年青,红果节节向上,画面前方的碗碟中有两只鲜美的寿桃,万古长青,福寿天成,有祝寿延年之美意。百合花一般象征百年好合,祝福有情人连理比翼,而在《百事皆好》中,百合的寓意更为包容,愿世间百事皆如愿合欢。
张朋先生另有一些极富生活气息的静物作品。他很喜欢鱼的意象:有些作品中鱼缸里有一尾小金鱼在自由穿梭,有些作品角落是煎鱼佳肴,无论何种鱼,都是借“鱼”表“余”,象征年年有余、富足充裕。《春风常在画人家》里的小鱼颇有意趣,大片浓墨铺排了花瓶的上端及底部,中部则以白描线条构成小鱼的鳞片,实在精妙。
器物之美,在张朋先生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在画花瓶等器皿时,他用笔极为简约,瓶身轮廓几乎是一笔勾勒出的。删繁就简的同时,非常奇妙地传递出器物的质感,透过笔墨的浓淡干湿,从寥寥数笔中就能感受到器皿的材质差异。正如明袁宏道编撰的《瓶史》提到的养花器具之别:“养花瓶亦须精良……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其次官、哥、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用以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就瓶结实,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宝古者,非独以玩。”张朋先生深入研究了器物的文化历史元素,作品中的器皿多样但皆具仿古之意,有的是半坡或仰韶的陶器,有的是青花或宋代名窑的瓷器,有的却是信手一画的随形器皿,或从白石画中找的灵感,或从八大山人笔下借的形质,无不传递出精神承具之美。
无论瓶花还是盆花,虽只采撷几朵,却也是自然之缩影,以方寸中见天地。追溯起源,瓶花最早是古人供奉祭祀所用,历经唐宋明清,功能越发丰富。文人因其山水林泉之心,将四时之花置于屋内,瓶花不仅是厅堂书斋陈设雅玩,更成为案头清供,承载了插花人外化的性情和附加的情感。相比于明清瓶花画作中常见的梅瓶、胆瓶等器型偏瘦长的花瓶,张朋先生作品中的花瓶更浑厚,有重量体积感,瓶身装饰天然古朴,不会与花枝形成过大的反差。《陶罐菊花》中偏方的纸张并未限制花枝,反而使其向横处延展,搭配云纹花瓶,更具“铜瓶添水养横枝”之韵。花瓶如此,更不要说尤为朴素的花盆了。明清画作喜好汇集多种花材,但张朋先生一幅画里的瓶中往往只绘制一种花,格外澄澈清丽。
明谭元春《瓶梅》诗云“香来清净里,韵在寂寥时”,文人插瓶花追求的便是幽静雅致。在这类作品中,张朋先生率性随意地用笔,勾勒出古朴浑厚的器物,加之清新雅丽的花朵,“朴、清、厚、率”之风完美融合呈现,臻于画境。由器及道,格物致知,张朋先生的简约器物之美,是他朴实无华内心的写照,清净、散淡、脱俗。沈从文先生著有文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据先生自述,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等等打交道。关于是否可以凝固时间,书中有段文字:“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唯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如何保管我们的记忆,如何安放我们的岁月,在案头,在纸间,在生活的角角落落。张朋先生在作品里将花枝嵌入瓶中,用艺术捕捉它们最明媚的一瞬,将易逝的美丽留传下来。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万般胜意,百事皆好。
作者简介:宋寒儿,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讲师,青岛市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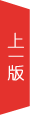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