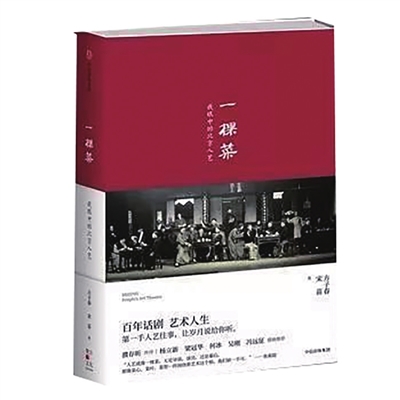张瑜
说起“一棵菜”,上点岁数的人大概会自动脑补:一棵大白菜。在很长一段时期,大白菜是北方地区冬季必不可少的家庭储备和餐桌主力。在中国戏剧界也有“一棵菜”,就是颇负盛名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
“一棵菜”这个说法,来自焦菊隐先生。1952年北京人艺成立时,副院长兼总导演焦菊隐先生从中国戏曲界借鉴并提出了“一棵菜精神”:剧院好比一棵菜,无论是菜根、菜心、菜叶、菜帮,都紧紧团结在一起,不分主次,共同为了艺术而奋斗。这样的概括非常贴切,大幕拉开,不光是演员在台上倾情演出,幕后掌管服装化妆道具、舞美灯光音响的师傅们都要“给力”,才能成就一台大戏。
2022年,北京人艺迎来七十华诞。这个时候,再读方子春、宋苗的《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一书,自有一种站在热热闹闹的庆典之外,听一段京韵念白,忆一番沧桑过往的静水流深。方子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父亲方琯德是北京人艺的元老,位于史家胡同56号的北京人艺宿舍,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北京人艺那些大艺术家看着她长大,她看着他们变老。当她萌生为出书采访他们的想法时,“大家”们仍像她小时候那样欢迎她,向她讲述北京人艺的台前幕后,讲述自己的艺术人生。焦菊隐、朱琳、蓝天野……这些中国话剧舞台上熠熠闪光的名字,被她用饱蘸情义的笔墨一一拂拭,擦亮。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有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北京人艺。《一棵菜——我眼中的北京人艺》告诉我们,北京人艺从建院之初就站在了中国话剧舞台创作表演的制高点,曾经拥有焦菊隐、老舍、曹禺等编导主创;涌现过于是之、朱琳、蓝天野等著名演员;创作编排了《茶馆》《雷雨》《天下第一楼》等经典剧目,这些都堪称新中国话剧发展道路上里程碑式的存在。
话剧表演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西方,我国在元杂剧之后逐渐有了舞台戏剧表演的雏形。20世纪上半叶,话剧由于表演简便易行,观者易于接受而兴起。正值国难当头,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从李叔同的《黑奴吁天录》到田汉的《名优之死》,从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到陈鲤庭的《放下你的鞭子》,题材各异、华洋兼收的进步戏剧对社会民众起到了正向的教育、宣传和鼓舞作用。
1952年6月,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若干支文艺队伍,无论是曾经在解放区扭秧歌打腰鼓的,还是曾经在“国统区”演舞台剧的,合并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这座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剧院里,昂扬奋进和团结奉献成为主题词和关键字。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努力克服自身方言习语的痕迹,自觉向京味靠拢;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等四大导演也步调一致,统一风格,联手打造了一座以优秀剧目为基底的、北京的、人民的艺术剧院。新中国十年大庆之际,北京人艺一口气捧出了《龙须沟》《雷雨》《蔡文姬》等八台献礼剧目,一举奠定剧院在戏剧界的地位。
在人艺的排练大厅里,一直悬挂着“戏比天大”四个大字,它不仅仅是于是之、蓝天野等老一辈艺术家的舞台执念,也无言地观照着后起之秀的接棒努力:它见证过冯远征跑了若干年龙套终于得到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却因为“挑帘”一个动作就重复了一个上午;它见证过在《人民的名义》里大放光彩的吴刚,在人艺舞台上一小段戏走了二十多遍还是不过关,烦透了的他甚至和导演说话都有了抵触情绪。后来,无数次的舞台实践让冯远征明白了“你要和你的人物每天生活在一起”的道理,他成为教师后这样要求学生,成为人艺副院长后这样要求年轻演员;同样,演出结束掌声响起的时候,吴刚明白了之前被迫反复练习并不是导演对他的角色演绎不满意,而是在磨他的心性,让他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一个团体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对艺术的敬畏之心薪火相传,高起点的北京人艺才能七十年始终保持高品质,成为戏剧表演的圣殿。
北京人艺在出品“京味”话剧方面的努力甚至是固执,有目共睹。其中当然有渊源的成分:建院排的第一出戏是老舍先生的《龙须沟》,而《茶馆》作为剧院“传家宝”,更是人艺每年庆生必排的大戏;其中更有发展和努力的成分:人艺第四任院长任鸣曾编导了《天下第一楼》《全家福》等多部反映现当代普通北京人喜怒哀乐的作品,他在阐述和总结剧院创排风格时说:“北京人艺坚持排演京味话剧,体现的是从文艺演出角度展示北京文化的责任和担当。”
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加重了每个人心底里的乡愁。这个乡,是没有城与乡二元对立概念的故乡,它也许在唱响八百里秦川的信天游里,也许在迷离细雨中探出墙头的一枝杏花里,也许铺陈在被踩得发亮的石板路上,也许掩映在贴着“风调雨顺国泰民丰”对联的柴扉后。然而方言一出,即便鬓毛已衰,离乡日久,人们彼此瞬间会有一种地域,进而是感情和亲情的认同。排演“京味”话剧,用京腔京韵演绎北京文化,保留京派底蕴,为北京人解锁乡愁,是北京人艺自觉承担和一以贯之的文化使命。
作者简介:张瑜,媒体特约评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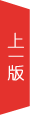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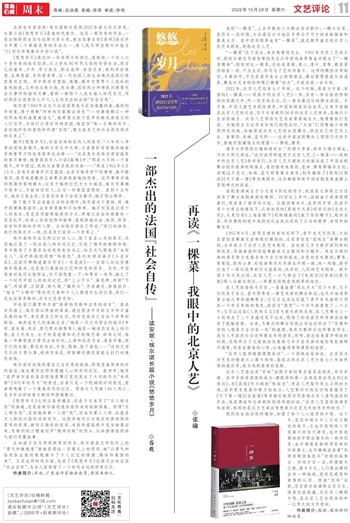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