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
《丹青记》是阿占首发于《中国作家》的中篇小说新作。看完后我就静了,生怕惊动画中人。阿占笔下的画匠入木三分,专业的描述堪比一堂精彩绝伦的授课,让人大开眼界。
汪曾祺先生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而非载体,强调语言即文学本质。《丹青记》最让人称道的恰恰是语言。真正的写作高手,是把诗词歌赋揉碎了,吸进去,化作自己的灵感,出来的,都是凝练的精华——阿占便是这样的高手。
动词是文学语言的灵魂。《丹青记》里动词的使用堪称一绝。“石愚微颔首,呲口酒”,一个“呲”字,涵盖了喝与品,且带了声音,彰显了性情的豪爽,使人物更加形象化。彦缺“沉默,寂然,眼神垂挂”,不用“下”字及其他,用“挂”字,既有神韵,又有动感,避免了人物的刻板和呆滞。季老板“行头上下都在抢”,一个“抢”字,强调了季老板的讲究,出风头,很有色彩感。逸之“将话题拽过去”,一个“拽”字,直接拟人化了,如临现场,似带风声。“甲大一口塞下最后四个饺子,把自己竖起来”,一个“竖”字,物化了人物形象,把甲大的粗俗暴露无遗。老穆和抱白“躲进灯影里捡乐儿”,一个“捡”字,描述了人物妙趣,憋着的乐,得不到酣畅淋漓,乐字有限,当然要捡了……《丹青记》里类似这些动词的使用,避免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提升了整部小说的高度。
《丹青记》整个布局,是以美院毕业生抱白的视角为主诉,带出在地的丹青群像。石愚,花鸟写意大家,代表着“庙堂派”,诸多社会职务傍身,其父是隐匿大师聋公,妥妥的“艺二代”,所以“石愚牢牢地把握着话语权”,未免有点骄横跋扈,常常自以为是。但时间总会辨出真伪,石愚终从神坛跌落。聋公和彦缺,是“在野派”代表人物,响当当的画界翘楚。聋公自由创作,人物绘画“个个天拙至极,每一笔都有神韵,甚至有神谕”。彦缺是真正的在野派,独来独往,“人,内敛沉静,画,凛冽宏大”。老穆,代表着不温不火的画界一大众,不争名夺利,心中有杆秤,敬业爱岗,八面玲珑。甲大,是民间艺人的代表,外表粗俗,却独具匠心,把俗常画成了“朴拙的美”。抱白代表的是新生代,经历了懵懂、探索、迷茫、顿悟,“在竹林里观自在,仰天望月,月微小朦胧,却可对谈”。《丹青记》里还有与画界搭界的一干众人,如收藏家兼商人季老板,书画评论家逸之教授,还有“猴王”“猫王”“马王”“驴王”“腊梅王”“葡萄王”,“虚名一浪高过一浪,均是被社会宠爱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参与,让整个画界像一个大染缸,真善美,假丑恶,统统倒进去,演绎着一处处令人咋舌的闹剧,由此,阿占揭露和讽刺了人性脸谱,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意义。
《丹青记》里,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彦缺。彦缺如庄子,行走在天地之间,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或道或仙,画意由心生,把大自然融入情怀,具有“史诗般辽远的悲怆”。但这种人注定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一场意外夺去了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才华。彦缺,令我抚胸痛泣。
小说中起起伏伏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美术馆。“美术馆三进式,园子嵌着园子。甬道兜转,串起了六栋小楼。”“前园正中的博也,后园正中的久也,皆悬山顶,琉璃瓦,凸字形平面。余为硬山顶,小灰瓦,清水墙。二进三的中园,东西各两条柱廊,可见彩绘点染,雕工画意。周遭亦成景儿。淡竹芭蕉衬映处,池水活络清澈。”除了美术馆,阿占不会忘记故乡的山海,她也让人物在崂山相见。“山路回环,车子盘上去。起初,海浮于树与树的罅隙,亮银般忽闪着。至半山腰,海雾渐起,海就退到了远处和虚处。继续蜿蜒盘桓,海雾弥漫开来,四周峰峦隐身其中,难识面目。”
我想,阿占书写《丹青记》时,想必眼前是虚设了一张大大的宣纸,容得她将人物逐个描画。人物与人物之间既相联,又独占一方,形态各异,千秋不同,不重叠,不遮挡,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真是一幅好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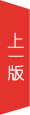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