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桦
翻开2022年第6期《时代文学》(双月刊),读到阿占的小说新作《残鸠》,乍看题目,给人一种错觉,以为阿占的创作要从都市边缘人物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故事背景锁定疫情肆虐的现实时段。一边翻阅,一边思忖:在当下,现实主义的难度多么大呢,这让许多作家选择了回避,于是就有了正史或野史的粗制滥造,有了苦咖啡写作、鸡汤文学的平面化书写,既安全又讨巧。阿占的小说显然不在此列,它们保持着一贯的语言纯粹性和优雅姿态,有一点任性,一点麻辣,加一点另类——犀利而又克制。
《残鸠》却与她的成名作《制琴记》不同,与那篇书写海洋的中篇《满载的故事》也不同,总而言之一句话,这篇写得沉实而富有韵味,通篇布满玄机,弹性和张力,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阿占最优质的一篇小说。小说一开始,阿占就漫不经心地排兵布阵,向水中撒下一张无形的丝网,波纹渐大,雾霭散去,人影也随之清晰。小说通过一个普通人物“他”的境遇,呈现残缺或不完美的人生状态,准确来说,即是表达出一种精神深处的复杂性——“六十岁刚过,他就说自己老了。”主人公“他”是一位半老男人,在外贸公司做老总多年,“稳中求胜,没什么功绩,也绝无闪失。”面对现实种种,厌离心日增,一门心思回归田园。当然,现代人的田园梦与陶潜的“归去来兮”有本质区别,陶潜还乡,是真正吃了苦遭了罪的,但心甘情愿,何等决绝!这是超凡人物与市井之辈的区别。现代人要实现田园梦,不过是退休前在郊区买幢房子,暂且远离喧嚣,要躲的东西太多了,躲意外,躲疫情,躲尔虞我诈,也躲温柔陷阱。说白了,这样的田园梦本质是伪命题,有些自欺欺人。
果然,小说中的“他”入住郊区,在体验过一段新鲜(种菜、养花、喂鸟)后,情绪很快归于乏味和无聊,于是往事显现,世俗的过往、暧昧的对象,那些乱七八糟的恩恩怨怨、残存的欲望、一地鸡毛的情感纠葛,又在白天或夜晚重浮心头,成为一种折磨: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怎么感觉离想象中的状态甚是遥远?若回城去呢,结果会怎么样?不不不,世俗生活与职场江湖,是如此繁琐虚无,无非是“赶场,拆台,凑局……油腻和嘈杂。”没完没了,早已彻底厌倦。这让人想起叔本华的那句名言: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徘徊。
在退出都市,“隐居”田园的过程中,一只失去右腿的花纹残鸠,奇怪而突兀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引发了“他”内心泛起的诸多共情——在自然界,残鸠曾经凶猛有力,目空一切;曾经用尖锐的喙吞食同类,伤害或被伤害。如今,残鸠蜷缩在一株桃树下发出哀鸣,偶尔发情,却力不从心。残鸠与世界咬合的能力在丧失,苍凉无奈而且悲壮。诸情诸景,小说中的“他”与一只残鸠在黄昏的光线里互相守望,灵魂瑟索不已。“他”的身体日益衰老,疾病不期而至,生命岌岌可危;“他”的精神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却又咬牙坚持。
《残鸠》就这么稳稳地,一个一个细节地,不落俗套地,把人物活脱脱地塑造出来了。语言富有筋力,是那种讲究却毫无做作卖弄的老到的语言!比如“开山搞钱,好在地产商端着小心,山的骨架没敢动,天成的畸石还在,水道未改,植被果木茂密处,房子都是绕行的,不曾有大面积杀伐。”比如“开门关门皆为深处,若无一颗在野的心,是住不下的。毕竟大多数人寂寞难消,又不懂得享受孤独。”包括几个次要人物,冉冉、儿子、发小、小舅子,也是几笔勾勒而神出,各有恰当站位。
对于阿占来说,《残鸠》所呈现的残缺美,或许是想借主人公“他”来表达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态度,或许是通过隐喻每个个体的精神残缺而对精神栖所形成关照,从这个意义而言,主人公“他”谈不上失败,也称不上胜利——那获胜的一方,永远是时间本身。
2023年1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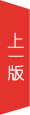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