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素尘
作为医务工作者,平日里见惯了病房的沉静与忙碌,唯有年关将至时,心底那份盼年的热切,才会像春芽破土似的冒出来。
打小在老家的田埂边滚大,许是沾了土地的性子,我们姐弟几个生得实在,活得也像脚下的土一样平常。后来举家迁到青岛,虽然一住就是四十载,但骨子里的年味,终究还是带着泥土的腥甜,半点没被海风冲淡。
小时候盼年,纯粹到就是馋那身新做的花布衫,盼着兜里能揣上几颗裹着糖纸的硬糖,更贪恋一大家子人终于能得闲聚在一起乐呵呵暖融融的亲热劲儿。
父母勤劳,考虑儿子多,房子便多盖了几处,于是每每过年贴春联就成了顶重要的大事。记得有一年,我约莫十来岁,母亲看我长了些个子,便把贴春联的“重任”交给了我们姐弟四人,还特意叮嘱:“门楣上的横幅得贴正了,这是咱家的脸面。”
领了任务,我们四个像得了军令的小兵,拿着春联,端着糨糊盆、握着笤帚,欢欣鼓舞地冲出院门。可刚站到第一扇门前,就傻了眼——门楣比想象中高得多,踮着脚、蹦着跳,依旧够不着分毫。我急得转圈圈,这时大弟突然一拍胸脯:“姐,我当梯子!”话音未落,他就稳稳地蹲在了地上,二弟和小弟立马凑过来,一人拽着大弟的一只胳膊当“扶手”,齐声喊:“姐,上!”
我踩着大弟的肩膀,手里攥着春联,心里又紧张又兴奋。大弟的肩膀不宽厚,我赤脚踩在上面都能感受到一份微微的颤抖,但他却努力挺直腰背,保持着平稳,我还记得二弟小弟的小手一边紧紧拽着他,一边努力扶住我的腿,“姐,往左点!”“姐,再往上挪挪!”“小弟,糨糊不够了,给我递点!”路过的邻居大爷哈哈笑:“你们姐弟这是搭了个‘人梯战队’贴春联呐!”
寒风里,姐弟四人冻得鼻尖通红,却忙得热火朝天。糨糊抹多了,红纸粘在手上撕不下来;对齐时没找准,春联歪歪扭扭的,又小心翼翼地揭下来重贴;二弟忍不住伸手去摸刚贴上的红纸,被我轻轻打了手背:“别碰,粘牢了才吉利。”从这屋的“福满人间”到那屋的“五谷丰登”,从柴房的“岁岁平安”到猪圈的“六畜兴旺”,每贴好一副,我们就围着转一圈,你一言我一语地点评,成就感满满。虽然棉袄上沾了糨糊、手上脸上蹭了红纸色,可看着贴得正正当当的红春联,想着这是我们姐弟四人共同完成的“大工程”,心里的自豪劲儿,比穿了新衣服还足。
夜幕降临,年三十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烟火气混着厨房里炖肉的香气,飘进每一个角落。父亲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噼啪声震耳欲聋,红色的纸屑像雪花一样飘落。母亲看着我们,眼里满是笑意:“今年的春联贴得最好,比往年都周正。”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年的味道,不只是新衣的布料香、饭菜的烟火香,更是姐弟间相互扶持的温暖,是齐心协力完成一件事的欢欣鼓舞,是家人围坐、灯火可亲的团圆。
如今的我从懵懂的小姑娘变成了资深的医务工作者。城市里的年,少了乡村的旷野之气,多了万家灯火的规整,贴春联也变成了用胶带轻轻一粘就能完成的简单事,再也不需要姐弟四人搭“人梯”。可每当我拿起春联,总会想起那年寒风里的协作,想起大弟肩膀的温度,想起弟弟们攥着衣角的力道。身为医务工作者,我见过太多离别与坚守,更懂团圆的珍贵。年的意义,从来不是丰盛的饭菜或崭新的衣物,而是那些与亲人共同度过的时光,是刻在记忆里的温暖瞬间,是无论走多远、隔多久,一想起来就心头发热的牵挂,这才是年最本真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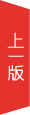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