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舒淇
手机屏幕的光,幽幽地映着我的脸。那家店的图标,朴素得有些过时,正是“老陕西面馆”几个字。底下稀稀拉拉的几条评价言辞犀利得很——“汤头寡淡,面不筋道”“臊子肉柴,绝非正宗”“不知如何能开二十年”。
这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我的童年是有声音与气味的。那声音,是父亲回家后,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咔哒”声;那气味,常常是周末午后,他牵着我走去那家面馆时,弥漫在空气中的暖烘烘的期待。走进店堂时总是雾气昭昭的,店里白瓷砖的墙面也被岁月熏得泛了黄。
父亲总会点一大碗臊子面。
面端上来,是海一般的大老碗,汤色红亮,上面浮着金色的蛋皮、黑色的木耳、黄色的萝卜丁与红色的肉臊,细韧的面条静卧其中。他饿也并不急着动筷,而是先拿起醋壶,酣畅淋漓地淋上一圈,再狠狠地舀一大勺油泼辣子,那“刺啦”的一声,仿佛是一曲盛宴的开场锣鼓。他吃得极专注,额上会渗出细密的汗珠,偶尔抬起头,用粗粝的手掌抹一把脸,对我憨憨一笑,说:
“杨帆,这面里有咱老家的味道,是乡愁哩。”
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叫“乡愁”。我记忆里的“乡愁”,不过是父亲宽厚的手掌,是那碗里他舍不得吃完的、硬拨给我的面条,是他把最后一口面嘬完,满足而又似乎带着一点落寞的脸。
初升高,像一道无声的闸门。我跟着母亲,去了城市另一边一个明亮安静的家。生活是向前流淌的,新的学校,新的朋友,新的习惯。那家雾气昭昭的面馆,连同父亲的“乡愁”,都沉入了记忆的河底,十余年未曾打捞。
直到今夜这偶然的相遇。
我盯着那些差评,心里止不住泛起酸楚,我好像忽然明白了,那碗在父亲口中无比正宗的、承载着他的“乡愁”的面,或许从一开始,就并非陕北高原上那凛冽的风与八百里秦川的塬以及陕南的水土所孕育出的味道。它只是父亲,一个从秦岭龙脉到海滨城市青岛打拼了半生的异乡人,用自己的记忆、自己的胃甚至自己的味蕾,所构建起来的一个美食的乌托邦。他口中的“地道”,是他个人情感认证的“地道”;那“乡愁”,是他一人独享的、旁人无法品咂的“乡愁”。
所以,它自然不合滨海食客的口味。它本就是一座孤岛,漂浮在父亲思乡的海洋上。而这孤岛,竟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固执地漂浮了二十年。
父亲也是一样吧。
我记得父亲似乎换过几次工作,住的地方也搬过一两回,可总离那片老城区不远。我曾疑心他是守旧,是懒怠。此刻却恍然大悟:他或许也只是在守着他的那座“孤岛”。纵使顾客寥寥,纵使评价刻薄,就像他这二十五年来,在我生活里那“顾客寥寥”的存在一般。
而父亲在疫情暴发期因病离青,回到他陕南老家的碗牛坝养病已有几年了。你终于又回到了那片浑厚的黄土地,吹上了山地的清风,喝上了真正的汉水。那么,当你病中虚弱、胃口不佳时,是否会想起这间开了二十年、味道蹩脚的老店?你是否会记起,你曾在这里,用一个虚构的故乡,喂养了一个孩子真实的童年?
那碗面,终究不是渡父亲的船,而是系船的桩。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在这异乡的城市里,为自己系下了一个念想。如今,船解缆了,回到了它本该停泊的港湾。
而我,关掉了外卖页面,没有下单。我知道,我等来的只会是一碗汤寡面柴的、平庸的食物。
我记忆里的那碗面,是那碗有父亲汗味、有童年光影、有一个平凡男人全部乡愁的面,是无人做得出,无人送得到的面。
窗外,是这座城市浩瀚的、喧嚣的、北方的夜。
父亲,今夜你在秦岭的月下睡得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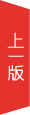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