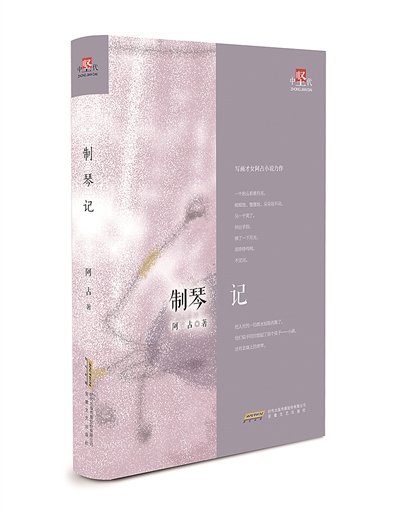对话阿占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知心的书写者,以漫游者、记录者、观察者、思想者的身份存在。在青岛,阿占就是这样的城市漫游者,独特的记录者、观察者与思想者。在她的“城市漫游”中,老海与老城相连,人与城,人与自然,亲密无间。
从散文写作到小说创作,阿占不断拓展着漫游的视野,从历史记忆到当下生活,从自然风物到人文景观,而其中不变的是对城市感性的觉知。她曾在散文中提及自己喜爱的运动方式:游泳,“躺在海面上,看到月亮升起,或者看到一架飞机穿过,或者一只孤独的海鸥,或者一些鱼跳起来,我都很感动,感到美得很忧伤。傍晚去游,会看到天边彩霞漫天的云象,即便是阴天的时候,也是水天一色,特别宽广,自然给了我很多鼓舞、力量和陪伴。”跑步,“一个人在山里跑着,感觉跟天地万物完全在一起,那些日出日落、和风细雨、狂风暴雨,一株植物的生发到衰落,你都会理解。”这一感性的体验也在小说的文本中延伸和拓展,在“湿漉漉”的“海气”与“潮气”中,达到城市、人、海之间纯然的融合。
“城愁”,阿占城市漫游中生成的另外一种感性与理性迭加的情绪。她将之概括为对于城市的一种深沉的情感凝聚,包含了关切、眷恋、忧虑、批评、期许……她将之融入了各具性格的小人物的书写之中。《制琴记》中的“琴痴”胡三、韩五,《墨池记》中的“疯中医”松菴,《满载的故事》中的“海猛子”满载,……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诚恳地、用力地活着,带着这座城市独有的人格气质。如阿占所言,文学与城市互文、共生,而她也将对地方历史认知悬空的“城愁”、对城市文明传承缺失的“城愁”以及对物欲淹没清心的“城愁”,汇于笔端,其中隐藏的则是对这座城市无尽的爱与眷恋。
践行散文小说化
“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真实的通往虚构的道路”
青报读书: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在你的作品中总能够感受到只有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才写得出的那种对于所居之城的感性觉知,小说《来去兮》一开场,关于老房子的“毛孔”的比喻,瞬间就能激活读者的感官。如果把青岛这座城市比作一个人,它的哪一点性格特质是你最想去刻画的?
阿占:上世纪三十年代,老舍曾将青岛比作“摩登的少女”,至今一百年即将过去,城市的少年感仍然很好地保留着。如果一定要抓取某种拟人的性格,我会取“游戏天分”,这种城市基因似乎更接近自由的意志。
青报读书:当以小说家的虚构视角来观察城市时,它与你真正生活的城有什么不同?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你更喜欢以哪种方式来描摹这座熟悉的城市?
阿占:小说表达的是心悟的真实,而不是眼见的真实。虚构之城有现实的影子又和现实各自独立。而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超越——超越了耳闻目睹的物理属性,得以去裁夺事件背后的真相,参与他者的命运,厘清一个时代的面目,管窥人类内心的隐秘,从而抵达艺术真实。正如劳伦斯所说的,“艺术家是个说谎的该死家伙,但是他的艺术,如果确是艺术,会把他那个时代的真相告诉你。”
只要是描摹这座城,无论虚构和非虚构,我都会乐此不疲。
青报读书:由散文创作转向小说创作,是不是每个写作者都会有类似的冲动,就像是由拍电视剧转向拍电影?散文和小说,这两种文体之间的转换,对你而言是轻盈的一跃还是漫长的积淀?
阿占:这应该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这里的必然,是指在经年的书写中无意识地建立了承前启后的路径,做好了相应准备,甚至生成了某种隐匿的契约精神;偶然则更像烟花一瞬,缺乏持续的内动力。我以为,由散文转向小说,将冲动付诸实施并找到培育这份“冲动”的方式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每个作家都在努力地寻找真实的通往虚构的道路。
另外,从散文到小说,说兼顾更准确。就像写作近三十年,我也在兼顾绘画一样。艺术是彼此的融合,相互的帮衬,内在原理与节奏毫无违和感。法国新文学文体实践就是“贯通”,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都属于拐点的标识。以往的散文创作中,我一直践行“散文小说化”,包括场景抓取和横断面连缀、独特的人物对话、细节提炼与白描、结构设置等等,力求刻画严整,而不致流于空洞,散漫,虚蹈,絮聒等。
“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这是明代李渔说的。小说的叙事结构涉及故事情节的排列组合问题,需要强大的坚硬的逻辑分析能力做支撑。要想写好小说,需要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还需要将阅尽苍生的经历内化为深沉的自悟与省思,在内心完成多次发育,进而写出带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共通”与“共痛”。
写深沉的情感凝聚的“城愁”
“我一直在写城,写城的当下与过往,写城中之人的失意和失意过后的希冀”
青报读书:从《制琴记》到《墨池记》,前者探寻隐于市井的精工匠心,后者是对城市书法技艺传承的演说,似都与城市的文脉关联。对于小说题材的选取有哪些特别的考量?
阿占:文学与城市互文、共生。某种意义上,文学是城市的产物。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巅峰,都是在城市造就并呈现的。从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到公元三世纪中期,古埃及的亚历山大一直是精神和心灵之城。普鲁斯特、福楼拜、歌德、莎士比亚、但丁等。都分享了亚历山大兼收并蓄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作家,他们在唐诗、宋词、元戏剧、明清小说里,也都分享了各自的帝都荣光。
我一直在写城,写城的当下与过往,写手艺人和痴怪者,写城中之人的失意和失意过后的希冀……我将此定义为蓝色城愁系列。相对于游子的“乡愁”,“城愁”是一种在地之愁,是现代人对自己城市的一种深沉情感,包涵关切、眷恋、忧虑、批评、期许等情愫,而不是简单地与忧愁画等号。
地方历史的认知悬空,是一种“城愁”;城市文明的传承缺失,是一种“城愁”;物欲淹没清心是一种“城愁”,静冷与喧嚣对抗,是一种“城愁”……这些我都在写。又因为对“泛艺术”领域的关注,“城愁”的消解或叠加就落在了匠人身上,并让他们成为使命式人物。
青报读书:目前在文本的表达和题材的选取之外,小说创作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阿占:只要选择了创作,挑战就会伴随始终,空中起楼阁,无中生有,耗的都是心血。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真相深藏于层出不穷的假象中,如何搭建闪转腾挪的叙事空间,又如何将叙事空间不断地打开,向着更为广阔的外在时空开掘。如何将内在与外在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持续实现完美的融合,如何做到在逻辑严密的叙事中又处处闪烁着人性的润泽与渡化……而这些,也是写作者的生命意义所在。
海教习远眺与回望
“海塑造了我的哲学体系和美学标准”
青报读书:海的意象几乎出现在你所有的小说作品中,如你所说,老城连着老海,青岛人爱海是基因里的爱。它会成为你的小说创作的标志性符号吗?就像是画家艺术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标识,艺术家的精神缩影?
阿占:至少近十年,会的。
青岛是极具辨识度的城市,以此为背景搭建进行写作,出笔落笔皆与众不同。
你看,不是每座城市都有一个“老城”,也不是每个“老城”都能面向一片“老海”;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两者之间拥有一间“老房子”,也不是每间“老房子”都流转着值得记取的人间故事。
与此同时,海教习自由,教习远眺与回望,海塑造了我的哲学体系和美学标准。
海的坏脾气也会随时发作,离岸流、天文大潮甚至能带来死亡,悲痛弥散,而这是人间的真实部分。在多部小说里,我让生命的顿悟、自省、提问都发生在海边,是本能,也是直觉,因为海边不需要搭建阐释生命诗学的现场,却会产生现场。
青报读书:《后海》这篇小说似乎又与其他不同,其中海不仅与个体的命运连接,更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变迁,承载着宏大的城市历史叙事。不仅把城市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故事发生地,而是把对城市的观照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联系起来。参与对城市发展进程的书写和记录,这是你所理解的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或者说是你的创作动机吗?
阿占:写《后海》,我考虑过“意思”和“意义”的关系。
所谓“意思”,就是呈现毛茸茸的琐细生活,最终反映出以海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所谓“意义”,就是具有哲思性和时代性,让小说中的人物参与时代构建,并成为海洋景观的内在组成。
可以说,在展现青岛城市特质之外,我一头扎进了以海为内核的深层伦理、情感结构与文化认同的景观书写中。
布鲁克斯曾说过,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生活的意义何在?要是一篇小说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望之至。所以小说一定要“有意义”,其指涉小说的思想、主旨,隶属于哲思层面,代表着作者对这个世界、社会、人生、历史、文化的一系列看法和见解。
此外,还关涉小说阅读者的代偿心理的需要。
青报读书:《来去兮》让评论界联想到了珍妮特·温特森的内省和卡尔维诺的轻逸。关于小说创作的个人风格倾向,是否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参照系?
阿占:全凭直觉,全凭内心的追寻与呼喊,不知道会相遇哪位大师,有时候,即便遇到了也是后知后觉,或永不知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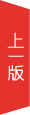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