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梁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作为华语武侠文学的巅峰之作,历经数十年仍被不断改编。徐克执导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以电影形式对其重新演绎,既是对原著的致敬,也是对武侠文化的一次现代性探索。影片以郭靖的成长为主线,聚焦“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核心命题,在视觉奇观与哲学思辨之间寻找平衡。
影片以“华山论剑”和“襄阳之战”为双核心,压缩了郭靖从草原少年到武林领袖的成长历程。同时弱化了江南七怪、黑风双煞等支线,突出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冲突、与黄蓉的情感羁绊,以及最终死守襄阳的悲壮抉择。这种改编使故事更紧凑,但也牺牲了原著中“江湖历练”的细腻铺垫。
影片围绕郭靖和黄蓉展开叙述。肖战饰演的郭靖摒弃了传统的“傻憨”形象,更加侧重表现其“大智若愚”的特质,通过三段式故事架构,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少侠形象。从草原时期的力量觉醒,到在中原时期的历练,再到襄阳决战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升华,让郭靖的形象不再只是武功高强的江湖高手,而是一位信念坚定的时代英雄。庄达菲版的黄蓉比较之前的版本,特别是翁美玲版俏皮古灵的形象,更加突出其谋略与深情。不再成为“靖哥哥”羽翼保护下的弱小,转而成为可以与之共担风雨的英雄伉俪,更加符合时代女性的审美趣味。
与两位正面角色相对的是,反派角色西毒欧阳锋则稍显脸谱化,为了得到《九阴真经》成就天下第一导致最终走火入魔,欧阳锋的悲剧性似乎是纯个人的,与时代形成了脱节,让观众在质疑和困惑中无法为欧阳锋找到正确定位。
导演徐克是华语影坛的“武侠奇才”。其作品以奇诡的想象力、凌厉的镜头语言、东西方美学的杂糅著称。他的审美情趣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充满现代性的解构与颠覆。
从《青蛇》到《新龙门客栈》,从《蜀山传》到《智取威虎山》,徐克的镜头中充满了东方审美的浪漫主义和西方的暴力美学。在光影与魔幻进而发展到现代科技的加持下,徐克的江湖世界逐渐立体起来。在《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徐克并没有引入过多特效,而是更多采用传统武功“气”的概念,以及中国传统水墨绘画的效果叠合,可以说是一次别具创意的大胆尝试。而在全片中,徐克既采用了工笔细描,也运用了大写意的狂放,在郭靖和黄蓉感情线索的勾勒上,极尽描摹之能事,而两军对垒环节,又用大写意的恢宏气势,展现战争的残酷与冷峻。可以说,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髓被他拿捏到了。
从影片深层次主题的探索上看,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侠之大者”是对集体责任的呼唤和追索,郭靖的选择不仅昭示了对自身所坚持的江湖大义的理解,也从家国情怀的角度展现了作为侠之大者的悠长气韵。他本可以与黄蓉栖身机关重重的桃花岛,当一对神仙眷侣,过起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但最终,内心的大义战胜了小家的牵绊,他决心要将个人生死寄托在两军阵前,哪怕赴死也要救人民于危难。就像他在劝蒙古大汗退兵时所说,两军交战,于人民无涉,那些无辜的人民,他们又为何要无缘无故地葬送性命呢?
金庸笔下的郭靖始终在“个人情义”与“民族大义”间挣扎,而电影将这种矛盾推向极致。影片通过蒙元铁骑压境的压迫感,将郭靖的“侠义”从武功高强升华为“以武止战”的牺牲精神。结尾处,郭靖站在襄阳城头独对千军的画面,既是对原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具象化,也是对当代观众民族情感的召唤。
郭靖的民族大义是我们需要赞颂和弘扬的。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个人小我和民族大我的关系是我们必须立场坚定的单一抉择。弃民族大义于不顾的人终将被后世子孙唾弃,而舍生取义,牺牲小我维护民族大义救民于水火的时代英雄,必将名垂青史,为后人所敬仰。如同司马迁所说的那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同海德格尔所言:“向死而生。”如同屈原在《离骚》中的悲壮慨言:“宁溘死以流亡兮。”如同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影片中的江湖或许从未消失,只是随着历史的长河,在泥沙的裹挟和打磨下,变成了如今波澜不惊的生活。它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而去,反而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并非完美,但其大胆的改编与恢宏的视觉呈现,为武侠电影开辟了新可能。它提醒我们:武侠的本质从来不是打斗,而是人在命运洪流中对“道义”的坚守。当郭靖在片尾说出“侠之大者,无非是明知会输,依然要战”时,金庸笔下那个理想主义江湖,又一次照亮了现实世界的幽暗。真正的武侠并不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而是在历经坎坷后,已然在内心葆有的那一份笃定。或许文艺作品的不断翻新,不仅是旧曲新唱,换一副面貌面对我们,更是从多元的角度,以一种适合当下的形式,传递出其朴实无华的本质。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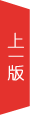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