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哈尔滨的人,大都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处处蕴含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在这座中国北方城市,街道两旁有着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还有造型独特的东正教教堂,以及掩映在林木间的俄式木屋。 20世纪上半叶,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正是他们把俄罗斯民风民情带进了这个城市。
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澳大利亚女作家玛拉穆斯塔芬的《哈尔滨档案》,书中详尽记述了流落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的命运和生活。玛拉一家1956年迁往澳大利亚定居前,就是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裔苏联人。
我与哈尔滨结缘于1962年。在上海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位于哈尔滨的林业部东北设计院,在那里工作了六个年头。那时,哈尔滨仍然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他们多数生活拮据,有的靠出卖古旧器物度日,有的靠养奶牛、奶羊维持生计。秋林百货公司是当时哈尔滨最高档的商场,里面也有俄罗斯族裔营业员,男士西装革履,高鼻深目,颇具绅士风度;女孩子穿着布拉吉,用碎花小丝巾系着头发,肤色白皙,非常亮眼。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这些人能够在科研单位或工厂企业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我所在的设计院就聘有俄罗斯族裔员工,包括一位年长的男工程师,两位年轻的女描图员和一位年长的女清洁工。
那位工程师早上准时来到办公室,大皮包往桌上一放,面前摆上一杯热水,便开始吞云吐雾,两眼直视前方。守株待兔的他很少主动与别人搭讪,只在青年技术人员登门求教时才解疑释惑。下班铃一响,则立即扬长而去。我一直不清楚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两位年轻美丽的描图员,和年纪相仿的中国同事相处十分融洽,经常相互开玩笑。问她们葵花籽为什么叫“毛嗑”?她们笑而不答。这是因为哈尔滨人背地里称俄罗斯人为“老毛子”,嗑瓜子是他们的“绝活”——不停地把瓜子抛进嘴里,瓜子皮就飞快地从嘴角吐出来,就像一部自动机器。这也许就是把葵花籽叫“毛嗑”的来历。
那位清洁工伊柳辛大妈,是一位勤劳和善的西伯利亚“玛达姆”。她的丈夫老王在我们设计院烧茶炉,是山东人。伊大妈嫁夫随夫,也说一口山东话。因此,谁遇到她,都乐意和她唠上几句,听一听她地道的山东话。
后来,随着局势变化,他们就被解雇了。1963年年末的一天,院长直接告诉他们:“从明天起,你们被解雇了。”从此之后,大家就再也没见到这四位。再后来,听说他们去了澳大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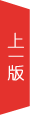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