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鹏
小时候的家在他乡,胶东半岛的一座小镇,朝听军号哒哒,暮听军歌嘹亮。朝朝与暮暮,我的家,就住在部队大院里,橄榄绿的情愫至今仍萦绕在我心中。
我生在军营里,长在军旗下。出生仅几个月,便随着爸爸的换防部队,从锁钥渤海的长山要塞来到黄海之滨的海防前哨。那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曾参加过著名的长津湖战役,我认识的许多伯伯都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可爱的人”。
听妈妈说,换防出发那天正是元旦。凛冽的寒冬里,妈妈抱着襁褓中的我,和许多随军家属挤在几辆解放车的车厢里,相互依偎着,一路颠簸。爸爸则随着大部队风餐露宿,步行三天三夜来到新的驻防地。
那时爸爸给谷师长当机要秘书,一个小生命的诞生,给周围的人带来些许喜庆。谷师长的爱人还给妈妈送来了一包红糖。爸爸请首长给我起个名字。那时部队大院有这样的习惯,后来,爸爸也曾为战友的孩子起过名。过了几天,谷师长用商量的口吻跟爸爸说:“就用部队换防的两个地名,各取一个字的谐音吧。”我没当过一天兵,却一辈子带着部队大院的情结。
我常常想,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于是才有了家国情怀。没有部队大院的熏陶,没有当兵的父辈的教诲,就没有我的成长。后来那支部队转隶青岛警备区,若没有那支部队的换防和转隶,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种轨迹。
那时的岁月,时光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在大院里,我度过了童年、少年,一晃就是16年。生活无忧无虑,心情欢乐放飞,四季轮回宛如成歌,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
我和小伙伴们曾看战士们打靶,抢拾弹壳,烫伤手指;曾爬到树上掏鸟窝,一脚踏空,掉下来摔到营房屋顶;玩躲猫猫时,藏进防空洞,差点迷了路;有一次玩沙包,小伙伴推搡了妹妹,我和人家打了一架;放秋假时,偷摘田地里的瓜果,被农民逮住,叫家长来领人……每每想起那些淘气的小故事,总觉得啼笑皆非,不可思议。
那些逝去的日子,生活的点滴,就像一颗颗闪耀的星星,在记忆的天空中闪烁。而大院里看电影,是我儿时印象里最清晰深刻的片段。
每当晚上有电影的消息,家属大院像过年一样热闹。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那个时代,人们对电影有着特别的偏爱。家家屋顶早早升起袅袅炊烟,孩子们早早做完作业,草草吃上几口饭,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天快点黑。
大院的大操场是夏天固定的放映场。以放映机为界,前面是家属区,后面是师部直属连队的观影区。尤其是家属区,孩子们早早就占满了长凳短凳、高凳矮凳,有的还搬来几块砖头石块占位,还有的干脆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大圆圈“圈地”,有时难免发生口角。连队的观影区则井然有序,战士们拿着马扎,喊着口号,或一路高歌,有序入场,一排排坐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尤其是连队间的拉歌,激扬高亢,此起彼伏,成了放映前一道亮丽的风景。《打靶归来》《黄河大合唱》《我是一个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响彻黄昏的天空。这些经典老歌我至今都会哼唱,现在还时常伴随着我的晨跑,那铿锵的旋律给予我力与美。
冬天看电影则在大院的八一礼堂。礼堂坐席有限,一般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批观影,遇到好看的电影,还能多看几遍。那时部队放映的电影,经常加映军事题材的新闻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万炮齐鸣、坦克隆隆的战火场面,我是踮着脚尖,站在礼堂过道上看完的。后来,我还聆听了战斗英雄巡回报告会。
有些内部军事教学片,地方影院不放映,有些影片首映时间也比县城影院早。记得还是在那座礼堂,上映武打片《少林寺》时,入场券十分紧张。看了一场后,我又和几个小伙伴爬到礼堂窗外,猫着身子,偷偷多看了两场。回到家,我默记写下电影内容,像写剧本一样,还有对话和情节描写。记不清多少页的手抄本,在同学间传阅。那或许是播种在我心田里的第一粒文字的种子。
部队大院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我念兹在兹。那里是我生命出发的地方,藏着我儿时最纯真的欢笑,是我成长的摇篮和心灵的港湾。那份来自部队大院的记忆,像胎痣一样,深深附着在我心灵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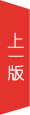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