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均鸣
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我属佛灯火命。倘若与各种木头亲近,不但生命力旺盛,事业线也会跟着一路上行。坦率地讲,我并不相信命理推算那一套,但由此产生的心理暗示还是有一些的。不停地收集各种木头是我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爱好。
有的人喜欢佩戴或把玩各种木制佛珠或手串,紫檀、黄檀、奇楠、崖柏、柘木、香椿木、花梨木……尤以海南黄花梨最显尊贵。而我对上述物件打心底里排斥,感觉太装、太油腻。
我喜欢收藏一些观赏价值较高的木雕作品。比如,我在浙江带回来一个红木雕刻的托钵布袋和尚;在井冈山购买了一只铁梨木老虎;在越南河内搜罗了一只酸枝木“喜上梅(眉)头”的镂雕笔筒。一次,一位同事从庐山买回来一个“邻家女孩”的木雕作品。虽然这件雕刻作品的木料有一道明显的裂纹,但那女孩面部的生动表情足以让我忽略这点瑕疵。几经缠磨,加价购藏到手。
有香味的木料是我的最爱。我曾委托朋友从东北原始森林里找寻到两块琥珀木。经过打磨后,一块显现出了明显的虎皮纹,被我命名为“虎虎生威”;另一块则神似一枚大芭蕉叶,被我称作“千秋大业(叶)”。琥珀木,当地人也称作松明子,是千年古松倒伏后,外表纤维渐渐腐朽脱落,木质内的松脂油渐渐向内沉积而成,有一种特殊的松香。因为易燃,这种木头过去常常被当地人用作火把,或劈成小木条生炉子。这些年,松明子改了个漂亮的名字后便身价倍增了。一块上好的琥珀木,动辄要价上千元。
其实,我也偏爱崖柏木。这种生长于山西太行山或四川大巴山里的树木,一般生长在人烟罕至的悬崖峭壁上。树根牢牢地扎在石缝里,弯曲螭虬的枝干则顽强地伸上天空,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如此,它们还是会在某个气候恶劣的年份走进生命的尽头。有心人通过悬绳冒险下沉到这些崖柏的生长处,小心翼翼地将其连根带枝地采集下来。于是,死亡了多年后的崖柏便以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再次复活过来。这种“扭曲中见刚正,飘逸间有含蓄,顽强中显个性,平实中藏骨气”的崖柏暗香浮动,沁人心脾。尤为珍贵的是,那些“根抱石”的崖柏最受追捧。另外,有些“沉水级”的崖柏骨料或有明显火烧痕的“雷击木”也价格昂贵,一木难求。我曾收藏过一块如意形崖柏木,长约尺余,通体暗红,油光闪闪,经过多年把玩已经包浆。凡是见过的人,无不啧啧称奇。
比如金丝楠阴沉木,被称为植物界的“木乃伊”。它是天然形成的绿色环保、密度较高(沉水)、物理力学性能稳定且耐腐性极强的木材。历史上,阴沉木一般用于小器物的制作,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皆把阴沉木雕刻艺术品视为镇宅之宝、辟邪之物。到了清代,甚至一度将其列为皇室专用之材,民间不可私自采用。否则,便有僭越之嫌。我曾有幸购藏过一块金丝楠阴沉木,用它制作了一对素面镇尺。金丝缕缕,暗香袅袅。抚触之下,滑如凝脂。这种文房用品摆上画案,绝对“嘎嘎有面儿”。
收藏木头,其实也是收藏一种情怀。那些深藏于远方大山深处的生命,经过风霜雨雪的岁月磨练之后,路途遥遥,千曲百折地赶来与我相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奇特的缘分。
尊重木头,就是尊重生命。热爱木头,也是热爱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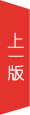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