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占
新的小说里写到了照相馆。对此我并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堂叔在照相馆工作,现在回忆起来,他大约是个无所不能的高手。第一次去照相馆玩耍,我刚读小学,照相馆的转门过于厚重,如机关暗藏的怪物——而我过于矮小,是被吞进去的。
孩子的瞬间记忆不超过两秒,随后迅速消失。有一小部分会转入短记忆,时长不超过一分钟。只有那些经过反复储存的,才会进入长记忆,可持续数分钟、数天、直至终生。奇怪的是,与照相馆有关的记忆都留了下来,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帆布门帘有夹层,隔断了外面的光阴和喧嚣。暗房里色调暧昧,以至于所有的物体都毛茸茸的,边缘感模糊。
堂叔把相机和冲洗罐放进“暗袋”,两只手在里面做着什么。暗袋来回耸动,似有戏法。我并不知道那些物什的专业术语,以及堂叔的操作流程所产生的意义,我只看到堂叔保持着平静,手法轻柔,却毫不迟疑。那种时候,暗房里总是出奇的安静,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有放大机发出的低鸣。
所谓暗袋是个不透光的黑色棉袋,有两只袖口,手从那里伸进去,进行程序化操作。后来我才知道堂叔是在拆装胶卷。胶卷最怕意外受光照射,稍有不慎,很多珍贵瞬间就报废了。
小说里,我设置了一对父子。儿子与我年龄相仿,小小的他亦被暗房的神秘气息所吸引,并且惊奇地发现,暧昧光线里的父亲竟是一个红着脸的羞涩男人,与生活中的样子截然不同——生活中那个脾气大的人,那个控制欲强的人,好像从来都不是自己的父亲。
儿子在暗房碰到的每个阿姨都漂亮,身上旋出一股子香气。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他请求父亲,尽快教给他全套的暗房工艺。于是,十五岁的整个夏天,他和父亲呆在密不透气的暗房,光着中年和少年的脊背,任汗水流成小溪,目击一张张白纸在光影与化学间的无限变幻。两个月的时间,父亲像在密室传授神功秘籍的高人,从古典的铂金印相、蛋白相纸制作到手工银盐放大、火棉胶摄影古法,一一展示。儿子并没有学会,但就此埋下了一颗匠心种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照相馆改制,小说中的父亲去了新加坡人的婚纱影楼。影楼营销噱头做得足,执行标准严格,拍照技术却乏善可陈,多用大平光掩盖面部瑕疵,美是美了,任谁拍出来都如电影海报里的公主与王子,或俯首低语,或温柔对视——却也不知哪个是哪个了,千人皆一面。
还好的是,新加坡老板也算讲究人,在纽约学过电影,三十岁之前做的都是导演梦,最终入了影楼行,钱赚到,艺术情怀却耽搁了。到影楼第三年,小说中的父亲在老板面前说出一席话——父亲说,好照片,三分拍七分做,从前七成功夫都在暗房,就跟现在电脑修图一样。“暗房里的活计,做得好,照片就漂亮,黑白灰那个润啊!”这个时候,老板一定看见父亲眯起眼睛,面部肌肉走势柔和,满脸沉醉状。这是少见的,父亲一向表情硬冷,来者不善的意味颇浓。
小说中的父亲继续说,好东西,都是见仁见智。反差大小,影调高低,分寸怎样把握并无量化标准。“多数时候,取决于技术和经验,取决于对事物、对别人的理解。老板,你的设备好,不会犯错,却也没有感情。”老板怔在半空。原本要冲泡高山茶,水已沸,父亲的话让老板停下了手上动作……接下来几年,老板借助父亲的经验,率先摆脱了千人一面之弊处,打出“人性摄影”招牌,植入心理学概念,一跃成为行业老大——小说后续,在此已无篇幅赘述。
写小说就是这么回事,以虚写实也好,以实写虚也罢,写的终究都是你们和我们的故事,大家一起在时间的舞台上跳舞,至死方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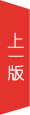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