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均鸣
韩疯子是我父亲的工友。当时,我父亲所在工厂的大院里有一个硕大的露天废铁堆,废铁堆里杂乱地堆放着一些回收来的废铁,另有一些本厂生产的有瑕疵的铁锅、铁炉、铁铲,以及锄、镰、锨、镐等。为了防止厂子里的工人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废物再利用”,韩疯子的职责便是将这些废铁进一步敲碎,然后整齐地码放在一边,等待回炉再铸新产品。韩疯子很尽责,每天在那个废铁堆前劳作,“不用扬鞭自奋蹄”,从不偷懒。当然,他也偶尔会歇息一下,选择一个相对干净的地场,淡定地坐下来。接着,便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酒瓶子,有滋有味地抿上两口。如此这般,一瓶散装高度白酒喝光后,下班的时间便也到了。韩疯子一日三餐从不喝酒,但却每天在零打碎敲中,不用任何酒肴便喝一斤白酒,这在当时也算是“高消费”了。好在他有个出息的儿子在白泉镇赵家村当书记,家里老伴也能下地劳动,不指望韩疯子的工资养家,韩疯子自然也便毫无后顾之忧地“潇洒”下去。
韩疯子并不疯,其实他的名字叫韩峰。有的工友们亲切地称他老韩峰,也有人叫他韩疯子。如果考虑到他每天被酒精泡得晃晃悠悠的状态,“韩疯子”的称号倒也似乎贴切。
我与韩疯子的首次邂逅时间发生在1976年。那一年暑假,我自胶东乡下去东北看望我的父亲,和父亲一起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白天父亲去铸造车间工作,我却不能去那里玩。因为,铸造车间里的熔铁高炉红红的铁水经常四溅,有一定的危险性。那种情况下,到废铁堆去找韩疯子玩便成为一个合适而又安全的选择了。当然,我始终称他韩大爷,父亲也叫他老韩峰。
我的出现,让韩疯子分外高兴。在他相对孤寂的工作中,有一个小孩子出现,让他的工作具有了一定的表演机会。他一边挥舞铁锤卖力地敲碎大块废铁,一边给我详细地讲解那些废铁的来历。我跟着他学讲东北话,他也跟着我学说山东腔。很快地,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讲的朋友。韩疯子是苦出身,没有上过学。听说我是一名三年级小学生,便认定我是“文化人”。他从家中带来了一些没头没尾的书给我看,我看完后,便让我讲给他听。面对那些繁体字,我囫囵吞枣、连猜带蒙地读,他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听。解老转、何大拿、刁世贵、毛驴太君、猪头小队长一一道来;从活捉解二虎到夜闯桥头镇,还有肖飞买药、智擒何世昌等等。另有高大成、杨晓东、关敬陶、金环和银环等一系列人物渐次走进我们一老一少的心中。那应该是我们爷俩心中一段无比快乐的时光,我们共同沉浸在精彩的故事情节里,紧张着,快乐着。不知不觉地,一个暑假就过去了。临别之时,韩疯子牵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撒开。他告诉我父亲,你要好好培养这个孩子,聪明,爱学,将来被推荐上大学也是有可能的。“我看,咱们厂子里的那个工农兵大学生也不如这个孩子。”韩疯子说:“我会相面,这孩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大耳垂轮,双目有神,将来一定会吃文化饭。”
似乎受到了韩疯子的心理暗示,我回到胶东乡下后,也开始坚信自己会吃上让人尊重的文化饭了。学习努力,做事也认真起来了。接下来便到了秋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4年秋天,我通过考试,顺利地上了大学。那一年,韩疯子已经退休且戒酒多年。他得知消息后,特意让老伴在家炒了几个菜为他佐酒。他说,老崔家的二小子考上大学了,必须正儿八经地喝一壶。据说,那次他喝了不到半斤白酒便已经酩酊大醉。他的儿子和老伴都说他老了,不能再喝酒了。他却“不认这壶酒钱”,坚称自己没问题,而是酒的质量不行了。
我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青岛工作,父亲退休后也回到山东老家安度晚年。关于韩疯子的消息渐渐少了起来,最后几近于无。去年夏天我回东北,特意抽空去看望我心中可爱的韩大爷。遗憾的是,他的儿子告诉我,老人家已于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临终前,他要求儿子不许火化自己。他的儿子也尊重了他的遗愿,把他的遗体偷偷地深埋在了一处庄稼地里。由于不敢起坟头,就以庄稼地里的某个电线杆为基准,正北20米处确定了老人家的最终归宿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年电力系统升级电线杆,木头杆换成了水泥杆的同时,电线杆的位置也相应地做了挪动。韩大爷的埋身地点目前已经无从确定,他的儿子也因违反规定,私自土葬父亲而被撤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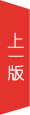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