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初中时在七中,我每天去接她,都要穿过天主教堂前的广场。女儿的书包很沉,上面有拉杆,底下有轮子,走过教堂广场的某一段石板路时,书包轮子会发出咔嗒—咔—咔嗒的声音,三个音节为一组,那个石板路有几十米长,会有许多组咔嗒声。
就是这个声音,唤醒了我关于火车的记忆。它与火车的车轮在铁轨上奔跑的音节节奏是一致的。我让女儿拉着书包在前面走,录了一小段视频,发在微信里,许多朋友都纷纷回复。有的说这个铁轨的声音催人入眠,有的说喜欢听火车的汽笛声。
对我们“70”一代来说,小时候基本都没有机会坐飞机,第一次出远门大概率是坐火车。火车意味着一段未知的旅程,小孩子都是期待未知的世界,所以火车的声音、火车的味道总是令人期待的。
到外地读大学,火车就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要坐四次火车,那时每次要坐22个小时的火车去上学,学生票是半价,恰好也是22元。当年的火车条件差,过道里站满了人,到了晚上还有人钻到座位底下。没有空调,许多人在车厢里抽烟,还有的人一上车就花生瓜子地紧忙活。
某一年我买了一个靠窗的座,坐进去之后发现这一个单元的10个座位,除了我之外另外9人是一大家,他们锅碗瓢盆带得齐全,甫一落座就把烧鸡、猪头肉、花生米、拌黄瓜铺排开,喝的是洋河大曲,一家人你让我我让你,嘻嘻哈哈地笑,吸溜吸溜地喝,吧唧吧唧地嚼,把我困在中间,耳朵没处躲,眼神也没处落,只好戴上耳机全程假寐。
1994年暑假,正是美国世界杯时。那时杭州到北京的32次列车即将改为空调车,车厢里的窗户都只能开上面一部分,下面打不开,车厢也换了新的,万事俱备,只是空调未开。7月初的爆热天气,一车厢人在大闷罐里蒸着,后来有人想办法,坐到座位的靠背上,这样打开上半部分车窗就能吹点风。这主意好,大家纷纷效仿,只是靠窗的座位行,可以手扶行李架,不靠窗的就全靠平衡能力,万一打瞌睡,免不了骨碌碌地滚下来。
除去放假回家,我们偶尔到杭州附近的城市去玩,也是坐火车。上世纪90年代初,长三角地区市场经济刚刚发力,苏锡常各地一派繁荣景象,或者说到处是工地,一片乱哄哄。我记得有一年去无锡,在无锡的火车站售票口,每个窗口旁边都有一把高高的铁椅子,像网球赛场上的裁判椅那种。而每个椅子上都端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遇有插队者便用竹竿敲击其身边的铁栏杆,以示震慑。老太太们并不是声色俱厉,反倒有点嘻嘻哈哈的,不太严肃。此等奇特景象,皆因铁路运力不足,车票供不应求,着急买票的人便想方设法加塞。
那时的火车上挺乱,有小偷,也有骗子。我曾亲眼见过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背着一大包红塔山香烟在过道里跑,后面有个穿警服的人追上去,一把摁倒。倒卖香烟要罚款,但是背烟的家伙说没有钱,于是香烟便五十块钱一条卖给乘客,充当罚款。我身边呼地站起来好几个人,激动地说,我要我要。那时的红塔山大概100块钱一条,50块钱当然便宜。不一会儿,一大包香烟就卖得剩下几条了。穿警服的人拿着剩下的几条在过道里吆喝:还有没有要的?正宗红塔山,五十一条,而被抓获的倒烟人站在那里,神情相当淡漠。这一幕我回学校讲给同学听,江湖经验丰富的同学告诉我说,穿警服的人、卖烟的人、开始时跳起来抢着买烟的人,都是一伙,烟是假烟,谁买谁上当。我觉得事情不可能这么险恶,还半信半疑,后来回忆起那个倒卖香烟的家伙,背的是一个半透明的尼龙袋,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背着一大袋烟,而那位“警察”穿的制服,似乎也不是乘警的制服。我身边的几个抢烟人,我依稀记得刚开车时,有人把他们叫走,难不成是现组的班子?这件事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不断翻捡,越想越觉得深奥。警察不是警察,乘客不是乘客,连红塔山也不是红塔山。多深奥。
火车运力紧张,卧铺票十分金贵,基本买不着。有一次我从青岛回杭州,坐的是青岛到上海的火车,旁边空了一个座位,我想让另外一个没买到座票的同学坐一会儿,那位上海乘客大摇其头,他掏出两张车票说,这两个座位他都买了,为的是待会儿能睡一觉。到了晚上,这位仁兄像一只大虾一样弯在两个座位里,长头发铺在座位上,大有跳水运动员做团身后空翻时的架式,我看这造型对脊椎和腰腹肌的考验较之坐上一宿更加严峻。
我想起这段经历是因为去年又一次坐火车去上海。现在青岛到上海的高铁挺方便,不再走过去的京沪线,而是从江苏沿海一路走过去,大大节约了路程。高铁时代的火车铁轨没有了咔嗒声。车厢里不再拥挤,骗子再无踪迹;车站明亮整洁,也无须执竹杖的老太太维持秩序。高铁上没有喝啤酒撕烧鸡的,也没有扎堆打扑克的。与以往相比,可真是享受。但是我仍然怀念坐绿皮火车的时光,因为那是我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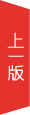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