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那日的天色,似乎有些异样。天空空荡荡,校园空荡荡,冬日的空寂填满了心脏。
荷花玉兰肥厚的叶片,卷曲,枯索,再无繁茂如盖的雍容华丽。银杏的铜枝铁杆倒是遒劲而倔强,沉默的凝视中自有藐视风霜的胆气和力量。
冷。风从四面八方来,不知是起于山巅还是行于水边。没有呜咽或者怒号之声,但是,能清晰地感觉到,在耳边,在鼻翼,在指尖,似剑气一闪,飞掠而过,凉森森,冷飕飕,连眼睛都是冷的。
离躯体最远的手脚似乎失去了依傍,伶仃地陷于苦寒之境。跺脚,搓手,将身子紧裹于厚厚的冬衣之内,亦不能抵挡无处不在的彻骨寒意。双手处于从未有过的恩爱和谐,不停地抚摸和揉搓之中,稀薄的温暖从手心传到手背。
非毕业班的师生早已离校,偌大的校园再无往日的喧嚣热闹。惟来去匆匆的高三学子,在寒气里苦熬。好在,还有平房教学区的蜡梅。青黄的叶子所剩无几,横斜的枝上,缀满了小小的梅朵。梅恍若沉静的女子,一袭素衣,款款行于苍茫的天地,柔婉,清澈。“梅”,似旧时戏文里白衣公子的轻唤,多情而温婉,微微抑制着怦怦的心跳。双唇开合之间,隐隐香气便幽幽而来。这一抹淡黄,是冷冬里的温暖,是人性中的柔软。
等梅开,等雪来,大概是冬之于我的意义。因为有梅,因为有雪,冷一点,荒一点,便也值了。可是,见惯了梅开,却等不到雪来。对南方人来说,雪来,不是看天气,而是靠运气。这么些年来,雪似乎早已把南方忘记,华美的银装素裹,绝尘的冰雕玉砌,仿佛成了北方的专利。
还记得,那个冬日下午,幽幽梅香里,阴沉的天空慢慢明朗起来,少见的空远辽阔。不久,竟下起雨来,淅淅沥沥。
冷风乱窜,教室门窗紧闭。正讲得起劲,忽见学生躁动起来,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惊奇,讶异。很快,目光齐刷刷扫向窗外。哇!下雪了!窗外,梨花乱舞。不,应该是梨花斜飞。大家不约而同站起来,扑向窗口,推开窗户,那清凉的花瓣便随着风雨还有梅香一起扑进来。学生们纷纷伸出手来,等待六角飞花坠落自己的掌中,啊哦啊哦之声,沸水一般,新奇而惊喜,激动而忘情,恍若迎接天外飞仙的驾临。尖叫,呼喊,惊叹,每个人都眼中放光,每个生命都活力无限。嘿!雪花落进了手中,仿佛玉蝶栖于花枝;咦,飞花消融,手中只余冰凉一点。这转瞬即逝的美丽之物!大家看着,叹着,那样兴奋喜悦,那样生动明艳!室内笑声不断,室外飞雪漫天。
不过五六分钟,飞絮烟消云散,仿佛刚才的白雪纷飞只是幻觉一般,真真是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大家意犹未尽,一双双发光的眼睛,依然星火闪烁,热气腾腾。
电视剧《欢迎光临》里说: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黯淡无光的,不能叫生活,只能叫生存。而那些配得上叫生活的,闪闪发光的瞬间,我们称之为奇迹。那节课讲了什么,那些年发生了什么,所有大事小情,有些随风,有些入梦。
不时浮现的,是那个初雪骤临的冬日午后,那一群闪闪发光的少年面孔。淡淡梅香,在冷寂之中游弋。遥远的北方,那只白色的大鸟似乎也嗅到了梅香,微微振动了一下翅膀。于是,片片轻羽,穿云破雾,飞越万水千山,若小小的精灵,轻轻落在南方的校园,落进那些沉寂已久的心田,溅起一朵朵惊叹,定格成记忆里闪闪发光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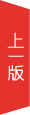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