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琪瑞
早年,父亲远在千里之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带着我们兄妹五个生活。那时,城乡通信手段极为落后,本地通话都成问题,更别说长途电话了,因此家里和父亲只能靠书信联系。可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写信回信只有让我代劳。
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识字不多,遇到生疏的字,我又不能用拼音,因为父亲没学过拼音。那怎么办?母亲点着我的额头,笑眯眯地说:“傻孩子,不会写难道不会画吗?”于是我们娘俩一起写信,她说我写,不会的字就“画”。
母亲说:“家里的老母猪生了一窝崽,需要粮食喂养。俺给你带着五个娃,也需要粮需要钱。一两个月没见你的信了,半年多没寄钱来了,你看咋办?”我照着母亲的话原原本本写,可“猪”和“崽”不会写,母亲摸过笔,画上大猪和小猪。
新疆的狼多,母亲从那里回来时,曾遭遇过狼。写信时母亲嘱咐父亲防狼,可“狼”我不会写,也没见过,母亲说狼是“铜头铁尾、豆腐腰麻秆腿”,不能画成狗。按她说的样子,我先在草稿纸上练习,直到母亲说像,才画在信纸上。
嫌画字费事,母亲有时干脆剪来花花草草,拼贴在信纸上。春天小院里的迎春花、杏花、桃花开了,母亲要表达喜悦心情,就采来黄的粉的白的花朵贴上;夏天麦子丰收了,就把金黄的麦穗剪去麦芒贴上;秋天枫叶红了、银杏叶黄了,就捡几片落叶贴上;冬天大白菜、地瓜入窖贮藏了,可这些东西太大,母亲就把白菜叶、地瓜叶剪成小圆片贴上,还乐哈哈地说:“你爸是农民出身,看得懂。”
后来,父亲叶落归根,调回了老家。他把我们给他写的信当作宝贝,也带回来了,整整一大箱子。我们翻看着那些皱皱巴巴泛黄的书信,不由哈哈大笑,这哪是信啊,简直是老和尚的百衲衣,斑斑驳驳的。只可惜这些剪贴画似的信,父亲病故后,按照母亲的意愿,都在父亲坟前烧化了。母亲幽幽地说:“是他的东西,都给他吧,也让你爸在那边不冷清,时不时念着我们的好。”
每到父亲祭日或清明节、中元节、年节,我们去给父亲上坟,母亲总要絮叨一番,交代我们这样不能少,那样不能落下,还要把她的话给父亲带去。按我们当地的风俗,母亲是不能去墓地的。
今年,我们去给父亲扫墓,八十岁的老母亲弓着腰从里屋蹒跚着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叠黄纸,说:“我给你爸写了封信,你们带去烧给他吧。”
母亲并不会写信,我们把纸展开,看到上面圈圈点点画有各种符号和小画,还有贴上的干枯花草。母亲有些腼腆的样子,朝我们挥挥手:“你们看也看不懂,只有你爸能懂,就是告诉他,俺快要去找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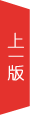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