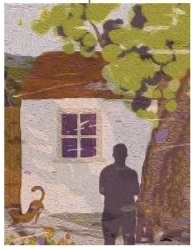王良瑛
我向来粗糙,简单地把世间动物分为两大类:凶劣与温善。前者如狼虫虎豹、老鼠蝙蝠;后者如羊鹿骆驼,以及鸟类。鸟类也不能一概而论。譬如食肉的鹰族就具有凶残的性情和作恶的能力,但多数温顺亲切,讨人喜欢。至于鸟中的斑鸠,那简直就是善中之善,令人爱怜了。
这只斑鸠,偏偏又失去了右腿,那就爱怜之中又多几分疼惜了。
但,失去右腿的斑鸠并不因此沉沦,更拒绝死亡,它顽强地与命运抗争。觅食必不可少,甚至本性的欲望都不放弃,于发情的春天,不停止地“咕咕咕,咕咕咕……”意味深长地鸣叫,果然就勾引来了一只雌鸠。可叹因为缺少右腿支撑,好不容易上到雌鸠背上,事不能成又滚将下来。被迫从此断了欲念,仅剩下吃喝保命一宗。转念一想,如果失去右腿的不是雄而是雌,显然这点饮食之外的欲望,大概不至于成为荒谬,可是偏偏是雄。这并非斑鸠的过错,而是阿占无情,用心太过残酷。
阿占是为了切合她小说中的那个人,那个男人。
那个雄性的人同那只雄性的斑鸠一样,由好到残,慢慢地残,直至最后差不多只剩下求生本能的“纯粹”。
这便说到了人。
人是什么?科学家定义:高级动物。
既是“高级”,自然又与“低级”不同。又是科学家说,“不同”的本质在于人有思维,有意识,因此也即有思想;动物没有,动物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有的只是本能。若真如此,恰恰戳到作为人的可恶之处了。
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自古至今,人们各持己见,争论无休。“人之初”是个无齿婴儿,尚无记忆,便无佐证,可以任你主观说东说西。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之初”总是单纯,单纯到几乎只靠本能左右行为,想吃就吃,想拉尿就拉屎,恼了就哭,喜了就笑,无论时间不管场合。到科学家们所说的开始思维,并且思维日渐清晰,有了意识,并且意识日渐强烈,才复杂起来了。复杂的重要标志便是对私欲——地位、名誉、财富、尊严等等的攫取。攫取非同小可,既广又深,因此手段也高明,明里暗里,你死我活。手段高明但不高尚,而且越高明越不高尚。内里肮脏,表面却道貌岸然,正人君子。这就需要掩饰,需要装扮,于是穿戴上盔甲,戴上面具;一层又一层,一个又一个,不断地穿,不断地戴。直到退出舞台,才长叹一声:人生至此矣,我从此“采菊东篱下”,“糊涂”起来吧。
是也?非也!
郑板桥“难得糊涂”大致是牢骚之言,世事不如意,仕途灰了心,无可奈何,“糊涂”了吧。陶潜的“采菊东篱下”,大致是自欺之语,自诩“心远地自偏”,其实心未远,否则不会去幻想桃花源。究其底,盔甲也还穿在身上,面具也还戴在脸上,未曾脱未曾摘。
但是,总得脱,总得摘。何时?灯油将尽,欲望皆灰,只有“命”的本能,“我”之本真的时候。而且,多是非自觉的,非主观意识所为。
小说《残鸠》,正是用“他”退休以后的岁月,表达了这样一段人生轨迹,心态变化。
曾经在外贸行业干了多年一把手的他,退休后住进了三年前就盖好了的山里的房子,以种植房前半亩小院为乐,为荣。“带上一只狗两只猫,吃自己种的菜,用老泉水泡茶”,展示一种退隐之态。但是,心“退”了吗?没有,还是用另一种方式端着装着,盔甲未脱一件,面具未摘一个的,而且也同“春雨初晴的早晨”那只残鸠一般,想起那位高品位女子于冉冉来。但因为体力不佳,种菜失去兴趣,半亩小院种上了木本,才开始叹气,老了。但盔甲和面具仍然未动,欲望也并未全部消退。真正摘脱盔甲和面罩,是经历了几次病,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差不多死过一次,意识到生命之尽头的时候。这时候,除了本能地维持,实则是消耗生命,其他念想已微乎其微,这才盔甲一层层脱掉,面具一个个摘下。不过,脱和摘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生命之神。
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桃树下喝茶,枯坐,打瞌睡,看院子里那只残鸠苟延残喘。
残鸠。
忽然就想起我十几年前写的一首诗——是分行的白话,不是诗,只是现今把分行的白话叫作诗,我也跟着叫作诗了——题目叫《游泳》:“不大不小的时候/知道了害羞/穿着短裤跳下水/游到对岸站起来/却是赤条条一丝不挂//七老八十的年纪/无所谓羞与不羞/脱得赤条条跳下水/游到对岸站起来/竟是衣冠楚楚。”
我猜想,若“他”看了,会苦笑着摇头,加上两句:“不在乎裸体还是穿衣/只知道活着是今天的唯一。”
阿占,一个小年轻,怎么对人生,对夕阳,洞察得如此透,如此狠呢?
作者简介:王良瑛,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有长篇小说和多部作品集出版。多件作品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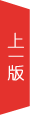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