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敏
三站印记:在流动中读懂非洲
1991年,法航的机翼第一次切开非洲大陆的云层,阳光像融化的金箔,铺满赞比西河的河面。我趴在舷窗上数着海岸线的曲线,那时不会想到,这片土地会成为此后半生反复回望的坐标——就像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一旦见过那片流动的粉红,便再也忘不掉。
赞比亚卢萨卡分社的日子,与铜带省的铁轨、赞比西河的涛声缠绕在一起。殖民时代留下的旧铁轨,与坦赞铁路的新钢轨在阳光下交错,后者的枕木下,埋着中国建设者的汗水,也埋着“友谊”二字的重量。我背着相机穿梭在市集,恰逢非洲大陆首次多党制选举。投票站外,人们举着候选人的海报往来穿梭,议论声、喇叭里的宣传声交织成一片,有人眼神里带着对未知的探询,有人脸上是按捺不住的躁动。这种从未有过的政治实践,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在民众心里激起层层涟漪——有新奇,有迷茫,也有对改变的隐约期待。
转身走进村庄,却见一位母亲蹲在猴面包树下,给怀里的孩子喂青黄的野芒果。“树会结果,雨会落下,孩子会长大”,翻译转述的这句话,后来总在我脑海里回响,像赞比西河的涛声,沉稳而坚定。
转至肯尼亚内罗毕,非洲总分社的灯光总亮到深夜。作为终审发稿人,“Final say”的签字笔握在手里,总觉得分量千钧。蒙巴萨港的发报机嗒嗒作响,渔民的独木舟与国际货轮在海面交错;桑吉巴尔的滩涂上,退潮后的水生物成了孩子们的玩具,笑声混着咸腥的风。去南非驻肯使馆办签证时,签证官Mr. Weiser(发音近“Visa”,倒像暗合了他的身份)总爱盯着窗外的合欢树,盖章时慢悠悠地说:“你们记者,总爱追着风暴跑。”后来才懂,他说的风暴,正酝酿在南非的土地上。
纳库鲁湖是常去的慰藉。成千上万只火烈鸟铺展在湖面,粉红的翅膀扑棱着,像流动的云霞,连天空都被染得发暖。有次遇见鸵鸟在湖边踱步,笨拙却执拗,倒让我想起那位母亲的话——大地不会辜负认真踩过它的脚。而远处草原上,长颈鹿正伸着脖颈够向高树的绿叶,身姿优雅又带着股韧劲,那一刻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非洲最本真的模样。
淬火:在历史褶皱里看见光与痛
1992年的南非,像一口烧得滚烫的锅。作为特派记者,我不仅亲历了这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关键节点,更较早以大陆官方媒体的视角,用《走马看南非》《南非投资环境面面观》《向比勒陀利亚进军》等报道(其中《向比勒陀利亚进军》是记录局势的特写),向国内读者揭开这片土地的面纱。博伊帕通惨案的血迹未干,22条生命的消逝让空气粘稠得像糖浆;可几个月后,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坐在谈判桌前,握手的瞬间,约翰内斯堡的教堂敲起了钟。我在一天内发完22条英文稿,手指在键盘上发抖,眼前晃过罗本岛的囚室——曼德拉住过的小房间里,只有一张草席,采石场的碎石在窗外泛着白光。
那时的南非,总在极致的反差里让人震撼。高速公路网密如蛛网,平整宽阔,行驶其上时,恍惚间会忘了身处非洲——当时它的公路发达程度,仅次于德国、美国。作为非洲大陆的“火车头”,南非的GDP一度占到全非洲的40%左右,约翰内斯堡的高楼与索维托的棚户区隔街相望,繁华与困顿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在阳光下同时反光。德班的黄金海岸线绵延千里,好望角的礁石上,巨型货轮鸣着笛穿梭,麦哲伦船队的航迹早已淡去,却带不走这里的繁忙。
同一时期的津巴布韦,还顶着“非洲面包篮”的光环,玉米与烟草堆满仓库,田埂上的拖拉机突突作响,谁也想不到后来的起伏。而纳米比亚的红沙漠与海洋交汇,美得惊心动魄,沙漠边缘的村庄里,孩子们却仍在为水发愁。这些景象总在提醒我:自然的馈赠从不等于必然的收获,就像撒哈拉大沙漠的黄沙下藏着石油,可若没有开采的技术与稳定的环境,宝藏也只是沉睡的石头。
最难忘那些细碎的瞬间:在卢萨卡市集,小贩会把最好的芒果偷偷塞给我;在约翰内斯堡的街角,陌生老人会用不熟练的英语讲曼德拉的故事;在桑吉巴尔的海边,渔民摇着独木舟归来,舱里的鱼不多,却坚持分我两条。他们的淳朴像草原的风,坦荡得没有杂质——后来才明白,这片土地的人民本就如此,在没有种族冲突和外来干涉的日子里,他们的笑容会比纳库鲁湖的阳光更明亮。
回响:从见证者到播种者
30岁生日那一周,我回到了北京。行李箱的角落里,还裹着从赞比亚带回来的猴面包树种子,是那位喂孩子野芒果的母亲硬塞给我的,说“种下就会发芽”。非洲的风好像跟着种子一起飘回了故土,往后的日子里,这份联结化作了遍布非洲的分社网络——几乎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有我们的足迹。
苏丹的喀土穆分社守着尼罗河的日出,索马里摩加迪沙分社的灯光曾在战乱中坚持亮过深夜,塞内加尔达喀尔分社的记者常去戈雷岛记录历史的伤痕,塞拉利昂弗里敦分社见证过战后重建的第一块砖;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分社、肯尼亚内罗毕分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分社、莫桑比克马普托分社……连南非都有两个——开普敦分社望着好望角的浪,约翰内斯堡分社守着城市的脉搏。内罗毕新落成的非洲总社大楼,就建在联合国机构附近,成了那片区域的标志性建筑,楼里的灯光与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一样,在夜里格外明亮。
这些分社像撒在非洲大陆的星子,用中文、英文、斯瓦希里语……向世界报道非洲,也向中国传递非洲的心跳。我们聘用了许多当地雇员,他们熟悉每一条土路的弧度,能听懂野芒果树下母亲哼的歌谣,有些还被派到北京总部交流,把非洲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西方媒体长期主导话语权的非洲,BBC、路透社、法新社的招牌曾随处可见,而新华社的存在,更像一种“南方的声音”——不居高临下,不刻意猎奇,只把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原原本本地说给世界听。
后来的职业生涯里,依托这些支点,我做了更多想做的事:在世界媒体峰会培训非洲记者,带他们看中国的梯田如何锁住水土;邀请非洲媒体人访华,让他们亲耳听深圳的厂房如何从无到有;全球新闻奖评选时,总想着多给非洲同行一些机会——毕竟,好故事不该被地域或资源困住。尼日利亚的同行指着课件里的滴灌技术,眼睛亮得像蒙巴萨港的灯;肯尼亚的记者写纳库鲁湖的火烈鸟时,会特意加上一句“它们的羽毛红得像我们的希望”。这些细节让我明白:所谓“讲好非洲故事”,从来不是替他们发声,而是帮他们握住自己的麦克风。
坦赞铁路的铁轨后来重新擦亮,列车载着货物与乘客轰鸣而过,像在续写当年的合作篇章。那位赞比亚母亲期待的“雨”,或许就是这样的技术与机会——当中国农技人员蹲在田埂上教插秧,当滴灌设备让沙漠长出蔬菜,当非洲的孩子能吃上自家田里种的粮食,雨就真的落下了。
凝望:向着丰饶生长的未来
书房的案桌上,一直摆着一尊非洲长颈鹿木雕。它站在台灯旁,脖颈微伸,前蹄似要迈开,雕工不算精致,却带着股鲜活的劲儿。我常看着它发呆,想起草原上那些真正的长颈鹿——它们优雅地踱步时,像在丈量大地的辽阔;一旦奔跑起来,蹄声能震得尘土飞扬;而伸长脖子够向高树枝丫的瞬间,又像在告诉世界:没有什么养分是够不着的。
多希望非洲能像它一样啊。像长颈鹿一样优雅,在多元的文化里自在生长;像长颈鹿一样有韧性,在风雨里始终挺直脊梁;像长颈鹿一样奔腾起来,让发展的蹄声踏遍每一寸土地;更像长颈鹿一样,够得着高树的绿叶,够得着天地间的养分,在阳光里茁壮成长。
有时会想起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50多个非洲联合国成员国,像50多颗星,在国际舞台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非洲统一组织(后来的非盟)的会议室里,各国代表用不同的语言讨论着同一件事:如何让这片土地摆脱贫困、战乱、干旱与疟疾。
而我们做的这一切——从1991年法航舷窗边的初见,到遍布非洲的分社,到一篇篇客观的报道,到为非洲记者搭起的桥梁——初衷其实很简单:让非洲走向世界,让非洲走向现代化,让赞比西河的水真正滋润干裂的田,让沙漠少一些,和平多一些;让被贩卖黑奴的历史记忆只存在于博物馆,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能堂堂正正、平起平坐地走向未来。
就像那位赞比亚母亲相信“树会结果”,我也始终相信:当非洲的田野里结满饱满的谷物,当港口的货轮载着本土制造驶向世界,当孩子们的课本里写满“我们的成就”,纳库鲁湖的火烈鸟会飞得更高,草原上的长颈鹿会跑得更欢,好望角的浪涛会唱得更响。
因为这片土地的丰饶,本就是全人类的荣光。而案桌上的长颈鹿木雕,会一直站在那里,像个沉默的约定——我们都在等,等它真正扬起脖颈,够到属于自己的那片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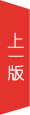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