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占
八月云疾,带来雨水和溽热,眼见着山体愈加丰腴,正是蝉鸣时节,已成十万军声,日日嘶吼,无从停歇。
我的小屋在半山之上,气流舒朗风自来,周遭植被密集,可谓山也青青,树也青青——这绵延无尽的青翠,却成了蝉之老窝,它们栖藏其中,将山谷变作天地间的巨大音箱,播放着青春与爱情的摇滚乐。别看个头小,声音嘹亮足可称奇,此起彼起,连成一片,一山,一空,一世界。即便是单只蝉的鸣叫,也能盖过山间的风声和水声。
每日大早,都有蝉歇伏在纱窗上,向我近距离展示那鼓动而轰响的腹尾,之嚣张,之雄壮,引得我每每自问,若乎小小的虫,何以有如此大的气力?莫不是在地下蛰伏多年,一朝出土,却又寿命短促,个把月行将死去,才将积攒的力量尽数发泄出来,倾力抢夺生命权和话语权,好教这世界知道它们来过。又或许,众蝉根本没有多想,只本能地鸣叫,高亢而单调,如同人要呼吸一般自然而然。
初入山的时候,一度不堪如此烦扰,却也无甚办法,唯心静自然安,久而久之,竟也习惯了,读书,写作,画画,并不耽误。
蝉鸣最盛时,通常在正午,太阳当头照着,山间热气蒸腾,蝉声愈发响亮,愈发欢闹,我怀疑它们在对歌,狂舞,山谷里充塞着一个盛大的派对。
到了傍晚,蝉声渐渐落下,偶有男邻居持竹竿,往树丛的高处寻觅,去捅树上的蝉。因蝉的颜色与叶片枝干相仿,总是颇难寻觅。到了第二天,蝉声会更加响亮,仿佛在嘲笑男邻居的徒劳。
只能等到大雨将至,山风四起,带着忽然的凉意,蝉们受了命令似的,集体收声。山间屏声静气,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坐于门廊前,看天边云海泱泱,竖着耳朵倾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溪水穿石的淙淙声,无名留鸟的咕咕声,皆浮动而起,原是被蝉鸣压制太久,让我有些忘了……
漏夜功夫,天放晴,气温复回,蝉声又起,依旧是那样高亢,那样单调,那样不知倦。我在漫山漫天的蝉鸣中喝咖啡,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
蝉鸣是古诗中常见的意象,或清朗,或凄切,多与诗人境遇相呼应,成为托物言志的经典载体。虞世南的《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司马迁《史记》中,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的形容,三国曹植《蝉赋》中,把蝉描述为“淡泊而寡欲”“与众物而无求”的高尚君子。除去中国诗歌中的独特意象,古代先民历来崇拜蝉,将其赋予了人文内涵与信仰,寄托着羽化重生的美好愿景。
每从山里回到闹市,蝉鸣声即被机械声和人潮声淹没了,这时候,再想起山里日子,那任性而天真的声响,竟成了记忆中最纯净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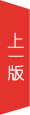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