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常温
青岛的红瓦,排布在起伏的山坡上,宛如一片凝固的火焰。这红色不甚鲜艳,倒显出几分沉着,大约是被海风吹拂久了,颜色便也学会了隐忍。
红瓦的来历,与德国人颇有些干系。1897年,德人强租胶州湾,便决意将青岛建成“东亚明珠”。他们带来图纸、机械,还有那固执的日耳曼审美。德国人做事向来认真,连屋顶也不肯马虎。他们引入德国的制瓦技术,在青岛设窑烧制。这便是大窑沟红瓦的起源了。
大窑沟的地势低洼,土质却极适宜制瓦。德国技师指挥着中国工人掘土、和泥、制坯,然后煅烧。火焰在窑内舞蹈三日,泥土便脱胎换骨,成了坚硬的红瓦。初时,瓦色鲜红如血,经年累月后,渐渐沉淀为暗红,倒像是被时光咀嚼过一般。
我在老城区的街巷中信步,抬头便见岧岧屋顶上那些红瓦排列如鱼鳞,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海雾漫来时,红瓦便隐在朦胧中,只露出模糊的轮廓,仿佛无数蹲伏的兽脊。这景象颇有些神秘,使人不觉驻足凝视。
德国人的红瓦屋顶,坡度很陡,据说是为了抵御雨雪。他们又在檐下设计精巧的排水系统,将雨水引向地面。每逢下雨,雨水从红瓦上奔流汇入檐槽,再通过水管泻下,那声音清脆悦耳,竟像是某种奇特的乐器。我常想,这大约便是建筑与自然的私语吧。
红瓦的颜色是会唱歌的。晴日里,它是明亮的男高音;阴天时,又转为低沉的男中音;而到了雨后,湿润的红瓦便成了温柔的女声,轻轻哼着古老的调子。这种通感,非细心人不能体会。德国人当年烧制这些红瓦时,可曾想到它们会在百年后,成为一个异乡人眼中的诗意?
青岛的红瓦与绿树相映成趣。德国人喜植悬铃木,其叶大如手掌,春夏翠绿,秋日金黄。红瓦从绿叶间探出头来,宛如害羞的少女面颊。海风掠过时,树叶沙沙作响,红瓦却沉默不语,只静静聆听。这红与绿的对话,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青山,碧海,红瓦,绿树。”康南海提炼青岛色彩的八个字,久已悬于旅行者的记忆之中。
大窑沟的红瓦工厂早已不存,原址上矗立起了商场与住宅。唯有那些老建筑上的红瓦,仍在诉说着往事。我见过工人修缮屋顶,他们将破损的旧瓦轻轻取下,换上新烧制的红瓦。新瓦颜色鲜艳,与周围的旧瓦格格不入,显得颇为突兀。但过不了几年,风吹日晒,新瓦也会变得沉稳,与它的前辈们融为一体。时间是最公正的调色师。
德国人在青岛待了17年。他们留下的红瓦却比政治更长久。这些红瓦见证了殖民者的来去,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却始终保持着沉默的姿态。我想,红瓦或许是睿智的,它们知道一切喧嚣终将过去,唯有美可以留存。
冬日,雪落在红瓦上,红白相映,分外鲜明。雪融化时,水珠沿着瓦楞滴落,节奏舒缓,好似自然的钟表。我曾在这样的午后,坐在阁楼窗前,看红瓦上的雪渐渐消融,露出原本的颜色。那红色在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暖,仿佛能驱散整个冬天的寒意。
红瓦也是有记忆的。它们记得德国技师的严谨,记得中国工人的汗水,记得战火中的震颤,也记得和平年代的安宁。每一片红瓦都是一页历史,只是无人能够解读。
如今青岛的老城区已成为保护对象,那些红瓦屋顶被列为文化遗产。游客们举着相机拍摄,赞叹这“异国风情”。他们可曾想过,美有时是带着伤痕的,就像这些红瓦,虽然美丽,却是殖民时期的产物。
夏日黄昏,我常常登临信号山,俯瞰青岛老城。夕阳西下,红瓦被染成金红色,整座城市仿佛在燃烧。这景象壮丽而略带忧伤。红瓦之下,是无数平凡的人生;红瓦之上,是永远流动的天空。
青岛红瓦,是凝固的音乐,是可见的气味,是沉默的讲述者。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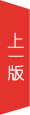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