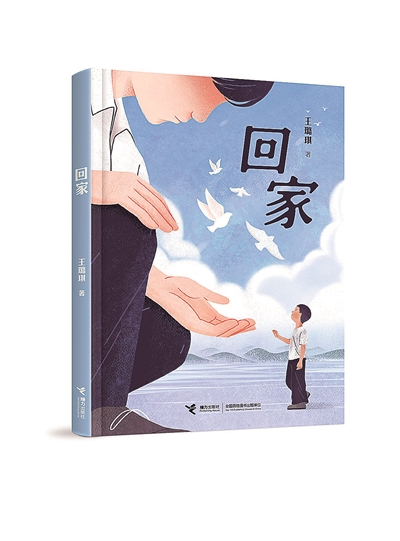十一岁那年,秦颂才知道自己竟是被“买”来的。他终于回家了,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里是他真正的家吗?断裂的人生如何重新连接?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王璐琪的新作《回家》讲述的故事。
在这位“90后”并不漫长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涯中,已经收获了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第五届金近奖、2015年桂冠童书、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第二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等奖项,而她作品中,年少的主人公如何直面现实世界的残酷,如何面对那些无法言说的内心伤痛,始终占据着主流叙事。她刻画弱小的个体生命于苦难磨砺之中成长的过程、与命运作战的勇气,同时也揭示童心与爱的真谛。正如她自己所说:当你采取平视的视角,就会看见弱小的孩子所拥有的超乎想象的力量。她告诉记者,之所以喜欢罗琳的哈利·波特,是因为她传递了少年的标配品质——勇气与爱。
而我们从《回家》中则看到更重要的讲述,关于人性中的阴影和幽微光芒,也是王璐琪特别想告诉孩子们的: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生命的模糊地带,也需要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
不避讳生活的灰度
“集体创造的环境,是一个人的总和”
青报读书:新出版的小说《回家》以一个拐卖儿童事件作为故事背景来讲述一个孩子的成长。回溯到几年前,《十四岁很美》所涉及的是性侵创伤这一敏感话题,《给我一个太阳》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遭遇校园霸凌的境况……以社会热点议题为创作题材,对于一位以少年儿童为第一视角的写作者来说,可能是更加困难的挑战吧。
王璐琪:这些创作题材是日常生活中的幽暗部分,若是家中有从事警察、一线教师、儿科妇产科或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等职业,就会发现像小说中有过类似遭遇的青少年儿童很多。并不是每一位受害者都能得到大众及媒体的关注,一例被曝光的案子后面预估有十名默默无声的受害者没被发现。
以少年视角写作,有一处成人文学不具备的优点,那就是视线的隐蔽性。孩童作为同样拥有智慧的人类,常因为体能上的弱小不具备“攻击力”而被成人世界忽视,其实儿童有自己的力量,去反抗命运的不公。
青报读书:你曾说儿童文学“应不避讳生活的灰度”,《回家》中被拐卖的孩子所面对的便是这一沉重的“灰度”。书写创伤或是社会矛盾时,如何平衡故事的真实性和少年儿童读者的心理接受度?对于现实的深度书写是否会有一个度的把握?
王璐琪:在犯罪、战争、疾病等极端且不可逆的伤害中,儿童需要更多保护。文学故事中,我们也要考虑儿童的心理接受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给孩子塑造一个虚假的、完美的世界。我们与儿童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这个信息爆炸、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儿童汲取信息的渠道已不再由大人掌控,作为成人,我们应该尽量真诚地展示真相,不要撒谎。文学作品应该让孩子了解真实的世界,只是在呈现社会不完美的一面时,尽量给予他们积极的引导,让他们心存希望。
青报读书:曾有人概括儿童文学创作——既要简单如童话,又要深邃如寓言;既要陪伴个体成长,又要塑造集体记忆——如同悖论,不可兼得。你如何来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王璐琪:在我看来这不是悖论。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在最简单的事实中,集体创造的环境是一个人的总和。
阶段性存在的文学无意义
“大部分中学生的阅读能力都和成人相当”
青报读书:作家张炜有一个观点,他说,“严格讲只有文学,没有儿童文学”。我们会发现,每一本儿童文学类图书后都标注了读者群体的年龄段,似乎在什么年纪就要读什么书,作家会因此限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吗?你如何理解张炜的观点?
王璐琪: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在我看来,小学高年级往上其实无需注明年龄段了,大部分中学生的阅读能力都和成人相当了。我的书除了不识字的儿童,大家都可以读。
青报读书:在AI当道的今天,提升人们的感受力和审美体验,似乎更成为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在《锦裳少年》里,你尝试书写昆曲的传承发展,更早的《刀马人》中,以界首彩陶作为叙事线索,关注传统文化似乎也成为你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王璐琪:我是从2015年意识到一些民俗文化,一些非物质文化在逐渐远离现代青少年的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复制粘贴的社会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无论去哪里旅游,都能在步行街上看到和家门口附近差不多的小吃摊,很多东西被同质化,我们被二手文化包裹。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似乎要通过“变异”才能“挤”到人们的视线中。我从《刀马人》《锦裳少年》《千窟同歌》等一系列历史文化类的题材写起,试图“传播”些什么,当然,我本人对这些很感兴趣,了解它们使我的精神生活充实。
青报读书:在你看来,艺术性作为衡量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标准,是否变得愈发重要了?如某位作家所言,这是一个需要以强大的诗性,纠正和对冲数理逻辑造成的盲角与误区的时代?
王璐琪:是的。除了艺术性,我们应该写出更具智慧,甚至超越时代价值观的作品,能够经得住时间的冲刷,从而留下来。回顾百年前的文学经典,无论国籍,能够留下痕迹的都是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作品,而非一时的畅销。儿童文学亦是如此,儿童文学若是只作为阶段性的读物,只在孩子某个年龄段出现,又匆匆消失,是毫无意义的,它应该使人时隔多年,依旧能够从中汲取到力量。这对作家来说很难,但是个好事,虽然整体市场受到了重创,可最终能生存下来的都是强者,不是吗?
真诚才是写作第一要务
“我始终相信图书的力量”
青报读书:现在看国内各大榜单,居于前列的儿童文学畅销书几乎无一例外都被国外的大IP占据。不知你是否也有自己钟爱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家,能讲讲喜爱她(他)的原因吗?
王璐琪:我喜欢罗琳的《哈利·波特》,因为每次翻阅都能让我做出正确的选择,“要有勇气,要相信爱。”
青报读书:在你看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目前亟须突破的瓶颈是什么,我们与那些具有全球热度的作品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一方面,是叙事模式?营销策略?还是文化的隔阂?为孩子所写的文学作品,如何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产生独特的吸引力?
王璐琪:说实话,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足足笑了三十秒。“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目前亟须突破的瓶颈是什么”这个问题换成“中国文学创作目前亟须突破的瓶颈是什么”,同样适用。我们可以自信一些,不管所谓的全球热度,先把作品写好——真正地写好,不为了得奖,不为了投其所好,不为了“升官加爵”……就真诚地写作,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
具有全球热度的作品有两种,一种是经典文学名著,这些名著显然已经经过时代的淘洗,留了下来,另一种由漫画改编,本身就有强大的读者群体,比如斯坦·李老爷子的漫威帝国,其粉丝文化和周边开采到了极致,全球范围内都有主题游乐园。说实话,作品和漫画我们中国有吗,有,且有很多,我们缺什么呢?想必这个问题轮不到我来回答,比如《西游记》这个超级大IP,除了几年前的动画片,其他的电影拍出来的能看吗?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青报读书:不知最近有没有去看《哪吒》那部动画电影,很想知道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会如何评价这个神话故事中的传统人物的走红。这是否也会促使你更关注儿童文学的视觉化表达?未来会尝试剧本创作或IP开发吗?
王璐琪:看了。很开心,很高兴,很骄傲。哪吒是有名的叛逆形象,同样属于叛逆形象的还有孙悟空。不知是不是因为平时国人都很压抑和温顺,所以格外喜爱叛逆的文学形象。就如同昆曲最繁盛的时候在明清时期一样,人们生活的压力都投射到虚幻的文学形象上,在虚无中寻找出口。其实现在正是读书的好时候,我始终相信图书的力量。
我有两部作品影视版权已经售出,影视版权费都快花光了,但是还不见拍摄的影子。说实话,国内无论是儿童电影还是儿童动画都处于冷场状态,《哪吒》系列是一匹大黑马,希望它能够带动这一块市场。但据我认识的一位制片人讲:未来还是很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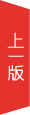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