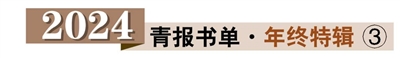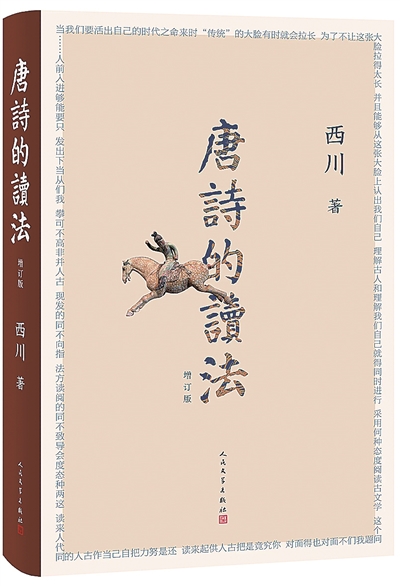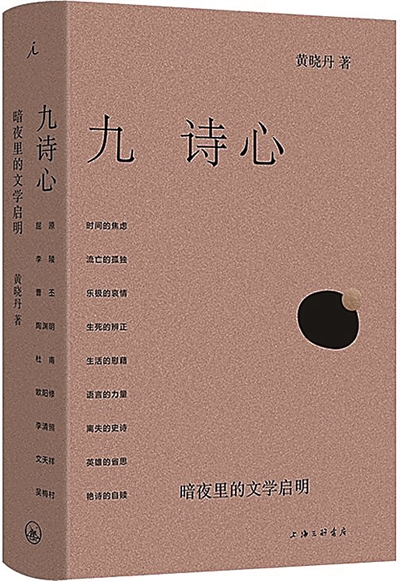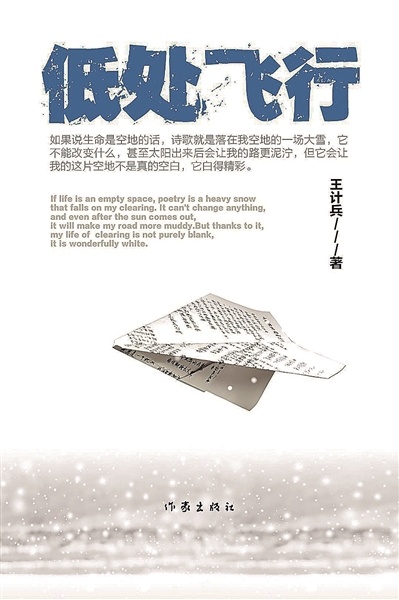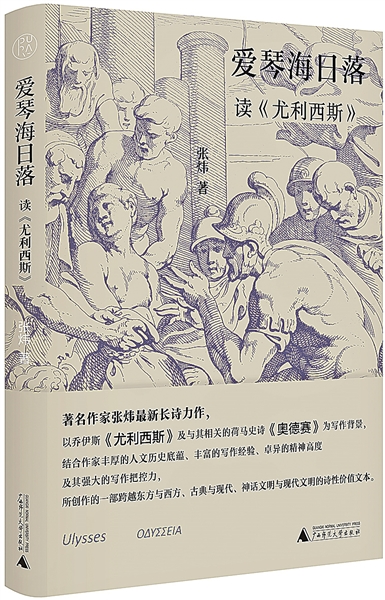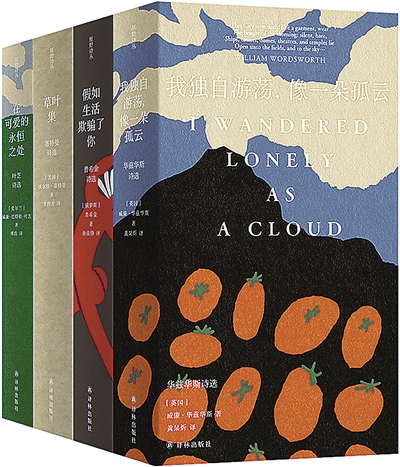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2024年,毕生发掘诗歌传统隐秘的叶嘉莹先生离世,这位小名唤作“小荷子”的百岁老人,为我们留下诗意饱满的莲子,继续生发的力量。她为孩子们精心挑选的古诗词在这一年再版,传达“诗无邪”“思无邪”的诗传承。她说,好诗的标准是“不受时空与个人经验限制,能激发人类永恒的情感共鸣”。人类对于诗歌绵延不绝的挚爱正源于如是标准的好诗句,它们翩然跨越古今中外,破除时空之界,从未远离。
于是在这一年,我们听诗人西川以他的世界文学视野重新讲述《唐诗的读法》,增订版中的杜甫个性更丰富,韩愈也变得愈发亲近;在黄晓丹的《九诗心》中,九位时代动荡中的诗人所面对的命运无常,死生契阔,孤寂流离,又何尝不是今天人们无力抵御的困境。
在现代诗歌的维度,诗人与他们蓬勃的诗情更让我们看到现实之外广袤的人类精神宇宙。张新颖的《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带我们进入“中国新诗”的时空,冯至、穆旦、卞之琳、海子、崔健等诗人及其诗歌的故事,与20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交织。
2024年是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120周年,聂鲁达的诗选《在我爱的世界上游荡》和文选《看不见的河流》面世,这位革命者炽烈的激情再度将我们渐趋冷寂的心灵点燃。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当世界上的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时,只有诗歌像爱情一样,可以表达最深刻的本质”,聂鲁达用诗歌言说爱情,以及政治、自然万物,向我们展现何为纯粹的热爱。这一年还是诗人米沃什逝世20周年,他在诗集《礼物》中传递另一种理性、博大的热爱,“爱意味着要善于凝视自己,就像凝视我们不熟悉的事物,因为你只是许多事物中的一种”,这本诗集依然以其一以贯之无可匹敌的精确与优雅,定义他所属时代的悲剧与美。
好的诗歌和诗人不会走远,总会适时重现,充当我们生活中的“嘴替”。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原野诗丛”,任我们在华兹华斯、普希金、惠特曼、叶芝的经典诗篇中徜徉,他们的诗作作为世界不同时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呈现。“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华兹华斯的诗句既是其诗选的标题,亦与今天的我们共情;惠特曼则自诩他的诗集吸收了千百万个人和十五年的生活,那种亲密,那种热烈,那种陶醉,简直无与伦比。
这一年,作家张炜完成了他的长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爱琴海日落:读〈尤利西斯〉》,究“纯诗”古今之变,探寻现代自由诗与中国古诗间的传承,这是他道阻且长却乐此不疲的诗路……
同样在这一年,我们也在素人王计兵的新诗集《低处飞行》中看到诗歌的另一种表达方向——一个个居于社会“低处”的平凡生命的现实境况。当诗歌进入具体的生活,它便营造了另外一种属性的能量场,足以抚慰每一个试图拥有飞行姿态的灵魂。
阿多尼斯说,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当现代人类面临许多问题找不到答案时,当人们感觉到无力时,只有它可能穿越一切找到答案。它是人类精神的代言,没有诗歌,就不会有未来。2024年,我们如此迫切地置身于诗的宇宙中间,这里是繁杂人生的避难所,正如诗人冯唐所言,“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在诗的宇宙,精神的内核不易被风吹散。
循着诗歌的传统,不迷路
2023年,作家张炜推出了《古诗学六书》,仿佛是在为他的新诗创作做着有关来处的铺垫,2024年,继《不践约书》和《铁与绸》之后,他的长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爱琴海日落:读〈尤利西斯〉》面世。他曾说,诗路是最难最长的,走得久了,有了一点觉悟,所以要好好写。探究现代自由诗跟中国古诗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张炜当下致力在做的事,在他看来,中国人写诗,完全依赖译诗的学习和模仿,终归不是办法,借鉴传统,才是中国当代自由诗的必由之路。
对于张炜而言,中国古诗的传统中有一个早已存在却被忽略的种属,那就是“纯诗”,在众多场合他都强调“纯诗”的意涵,将之视作现代诗歌的发展方向。而这一被认为伴随现代自由诗成长而出现的概念,实则早已存在于古风和律诗当中了。“它不同于一般的叙事言志诗,而是有着相对隐晦的语义和多重诠释的空间,以及复杂精微的审美指向”,在形式上却又延续古律朗朗上口的语感,从这层意义上讲,《爱琴海日落》便是建立在古诗传统之上的关于“纯诗”的一次汉语淬炼。
在这部新诗作中,张炜与乔伊斯共情:“书生的能量和无力总是并行的。《尤利西斯》在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里,并未因其晦涩而遭受冷寂,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得归结于普遍心绪:许多时候人们会觉得自己正与乔伊斯一起蹉跎,一起悲哀。文明的演进如同艺术本身,它难以线性发展,也不会简单地接续和进步,这当是人类的哀伤之源。”
言及长诗《爱琴海日落》写作的当下价值和意义,张炜回答:“数字时代把物质主义催生的后现代也赶到了角落,它无处可去了。那些俱已成为往昔的浪漫,看破和再看破,而后又会怎样,这是诗人们尝试回答的。空前的嘈杂覆盖了星空,真实的情形是星空还在,我们自己去了哪里?这难道不是当代人最该追问的吗?”对于张炜而言,诗人存在的意义或许就是,以一种朴实认真的态度和勇气,处理所有深晦艰巨的问题。
诗人西川也在思考关于诗人和诗歌传统价值的问题。在这一年的诸多采访中他都反复提及《唐诗的读法(增订版)》的写作动因:是反感不断有人拿唐诗和新诗作比、质疑有实验色彩的诗不是诗。在最近一次对话中他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天如果你能够背很多古诗,别人会觉得你是个大才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写诗的人,基本上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傻瓜,是个笨蛋。”他表示,这样糟糕的文化处境,更警示我们有必要重返唐诗写作现场,对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些长期困扰当代创作的问题,给出符合今天的视野、智力水平、精神水平的解答。作为一名新诗的写作者,西川坦言,自己对古典文学的好奇心指向的是它的生产本身。每一位写作者都有他的当代生活,如果不了解古人说话的对象,实际上就摸不清古人的工作性质,也无从获得古人创造的秘密。
对于诗歌传统的剖析也在张新颖带来的“诗的消息”中呈现,在《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里,他为我们上了一堂有关“中国新诗”传统的公开课,提出想要对一首诗有更为细致、准确的解读,就需要对诗人的经历、写诗的背景,乃至改诗的过程有所了解,如是才能明白,胡适《蝴蝶》里那个“很大”“又很质直”的情感到底是什么,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柔美感觉究竟来自于哪里。他引用冯至“十四行诗”中的句子,向我们说明诗的定义,是那个“可以给那些泛滥如水一般,没有固定形状的生活、情感、经验与思想以某种定型”的瓶子,也是“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有穆旦的诗句,“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这句诗也出现在作家金宇澄那部著名小说《繁花》的封底,金宇澄曾表示:他非常喜欢这首诗,对于语言的“可能”与“不可能”,纠结,折腾,充分说明了孕育《繁花》的艰难兴奋的历程。这或许是诗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传统,得以传承的另一种体现。
重回古诗现场,蓄能量
2024年,源自古代的盎然诗意依然固守于书页间,千回百转,回味悠长。
站在古今之间、诗歌“结界”之处的诗人西川,为他的旧作《唐诗的读法》增加了近一倍的文字量,而他所力求的并非对于唐诗本身的解读,如他所言:“我是一个实操的人,我自己写诗,所以我关心的是唐朝的诗人们是怎么工作的,他们的诗歌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他们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那么,我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我怎么工作,我的工作和公众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和社会生活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一个对称的问题,它们之间有一种对称的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西川在杜甫身上读出更丰富的人设,而韩愈,在他看来似乎被今天的人们轻视了,尤其是诗人精神世界里那种今人鲜有的久违的能量感。书中有一篇专门提到韩愈所写的《石鼓歌》,这是韩愈所开创的一个诗歌小传统,后辈的诗人中间,许多在模仿韩愈,加入到石鼓歌的写作序列中。诗人欧阳江河如是评价《唐诗的读法(增订版)》:“民间经常说‘招魂’,我觉得西川的读法比‘招魂’还厉害,他让古人从我们认为已经尘埃落定的、冰镇的状态中复活了。”
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古诗之所以百读不厌,正源于它镜像映照出今天人们与其相似的人生之境。黄晓丹《九诗心》中的九位诗人,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吴梅村,跨越朝代,于时代动荡的阵痛中求索人生方向,他们在各自的困境中,用文字开辟出一种可能性,“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如:曹丕面对无常时所持的人间清醒,“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这里没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高洁理想,而是所有人,所有种类的人生。天高地远之间,人渺小如飞鸟,且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栖息在随时可能折断的枯枝上。在“阳春无不长成”的背景之下,万物繁荣而生命荒诞。再如:陶渊明处变的达观,“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的春日,“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的夏夜,对生命本身的欢庆,是所有人生意义的起点。“尤其在目标受外在限制,无法实现之时,人即会遭遇意义与动力的双重缺失。此时,回到生命本身的活泼,就成为人生摆脱停滞,继续开展下去的关键”,在作者看来,陶渊明在晋末写出“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写出“稠花乱蕊裹江滨”,“诗酒尚堪驱使在”皆是奇迹。“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还有一直被课本认定为沉郁的诗圣杜甫,实则也有着慰藉的力量,在安史之乱中度过人到中年的八年,他并没有终将胜利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人告诉他战争何时结束,他靠什么获得安慰?……他还独自处理了更大的时代命题:如何面对黄金时代已经永远过去的事实。在黄晓丹看来,“王维、李白这些得盛名于开元、天宝时代的大诗人是盛唐物质与精神生活最好的记录者,但他们被过去的经验困住了,无法再面对安史之乱开始后不够好的世界,杜甫却一边追忆,一边告别往事,开启中唐诗歌的新境界。”
2024年还有两本关于大唐诗境的新著,分别来自薛易的《大唐诗人行》和六神磊磊的《唐诗光明顶》。它们同样延展了去年“长安三万里”的“诗友会”,带我们重回历史现场,再度感受千年前那个虚实相交、热气腾腾的诗意江湖。前者更让我们看到自初唐到安史之乱百余年间四十多位诗人的趣闻轶事,名篇佳句背后的人事变迁和历史波澜。唐诗即是人生,在唐诗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接过这些从时间中漂流而来的诗词,我们得以看见生命那古今统一的面貌,并由此想见:在历史上,或许正是诗的创造本身,助力诗人内观己身,努力挨过忧患困苦,走向内心的从容与澄明。
生前一直强调“诗教”的叶嘉莹,在今年再版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中选入了那些貌似不宜被孩子们读懂的诗作,包括王安石的11首作品,据说,这源于她早年困苦时曾受王安石一诗点醒灵光,因此便生此执念。而实则这也是叶先生作为编者一贯的诗词观:传达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生命的感发力。她个人为其所感动召唤,深信其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这大约也是所有古诗编写者的初心,即与古人能量相接的一份诗心。
捕捉可触知的真相,为了爱
在2024年,外卖员王计兵将他的平凡日常化作诗,诗集《低处飞行》在琐碎中创造了属于平凡人的浪漫。天地,人间,生命,在同一个空间里展开,日常的物象,被提升到一个更宽更广的视角去观照,留下唏嘘的感叹和深沉的思索,这或许就是诗歌进入日常生活时充满温情的样貌,也是蓬勃的生命在热爱中该有的样子——他将生活的细节、人生的百味变成或短或长的诗行,记录自我、记录对具象生活的感知,也记录时代。
这也让我们联想到西方诗歌最原初的样貌,在新出版的“原野诗集”中,译者黄杲炘在《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华兹华斯诗选》序言中讲述18世纪末诗人那本惊世骇俗的《抒情歌谣集》,这本诗集里,年轻的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摆脱了形式和内容上的“繁文缛节”,提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并在序言中公开宣称“这些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华兹华斯以此开创了探索和发掘人的内心世界的现代诗风,而他更新的不只有文学风格,更是观看世界和理解人类普遍生存处境的方式。
柯勒律治这样评价华兹华斯,他的诗歌的价值在于一种力量——能够将心灵从惯性的麻木中唤醒,使之关注我们眼前世界的美丽与奇迹。经典如此,平凡如王计兵的真情流露亦如此,这正是诗歌给予人们的礼物,这份礼物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那就是极具生命力的热爱。
2024年,透过诗歌,我们得以纪念两位全力去爱的伟大诗人。智力诗人聂鲁达,他的诗集与文集在这一年同期出版面世。他被描述成一个行动者、思想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情诗写作者,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他的想象、意象、语言、情感,对于他所在的国度,是与《诗经》以及唐诗宋词具有同等价值的存在;在8月我们纪念米沃什逝世二十周年,两册小开本的诗集《礼物》和《但是还有书籍》收录了诗人创作于1931年至2001年间的336首诗作。米沃什的诗歌,无论是描述在波兰度过的少年时代,还是战乱中华沙的悲痛或他对信仰的追寻,都令人感受到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平凡人生的生命力,年少时他愤怒写下“在我们剧烈跳动的心中,既不会有春天,也不会有爱情”,但依然对生活表现出全力的热爱:“这太少了,只活一次太少了。我愿在这悲惨的星球上再活两次。”在豆瓣上,有读者感慨:没有人能拒绝这样蓬勃的爱与恨,即便老去,他诗中的生命力依然不减:“是的,我想做一个五种感官的诗人,是的,思想比柠檬这个词的分量要轻,这就是我为何在词句中不去碰水果。”
在米沃什看来,诗歌是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诗歌的意义在于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它的目的就是,而且只能是,拯救。” 他的诗跨越了20世纪,把过去和现代相连,把自己与读者相连,对抗混乱与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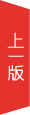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