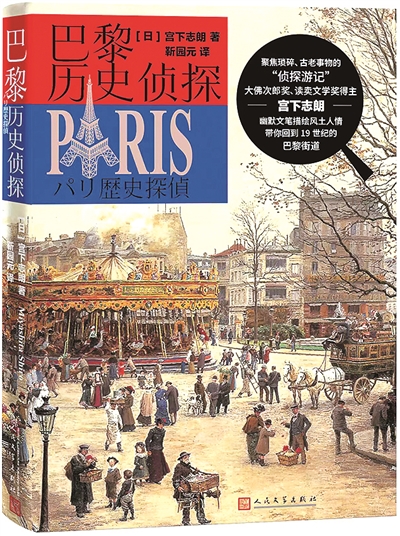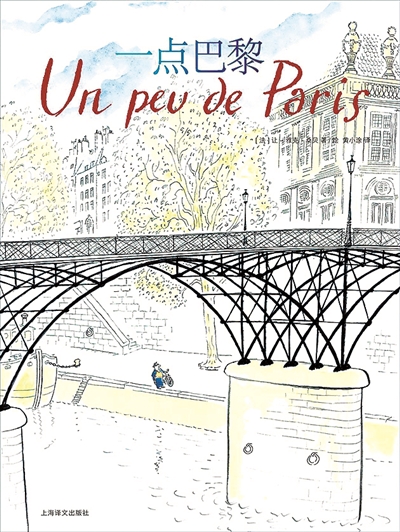□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巴黎是一个世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1540年访问巴黎后发出如是感慨,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既能弘扬美德,也能包容罪恶。
类似的褒贬合一的评价贯穿巴黎历史时间:蒙田说他“喜欢巴黎温柔的瑕疵及其一切”;伏尔泰认为,巴黎“一半是黄金,一半是垃圾”;拉伯雷说,“对死亡来说巴黎是个坏地方,但对生活来说巴黎是个好地方”;而21世纪日本作家宫下志朗则在《巴黎历史侦探》一书中表示,“巴黎是一瓶香气馥郁的美酒,我想探寻酒瓶底部的沉淀物”……实际上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赞誉总会超过失望,今天依然如此。就像面对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时那样:新奇与审视、惊喜与侧目总是伴生,人们无法回避被无数经典勾勒摩挲、文字塑就的巴黎的伟大,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这座被冠以“世界的头脑”“极大的奇迹”的城市的真实历史与现实认知的匮乏。在他们看来,巴黎代表了一个自由创造的符号,一种敢为人先的意志,一种谜之自信。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或许是一个契机,让我们跟随历史学家,城市建筑规划师,文学艺术界、时尚界人士的脚步,开启一场非比寻常的城市漫游(要知道流行于21世纪20年代的City Walk,也正是300多年前巴黎人的发明),将用想象力和创造力建构的城市与其原本的真实面貌两相对照,也让我们暂且放下文化的偏狭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重新梳理文字中的巴黎,阅读理解一座超出单一概念的城市——另一种不同于我们的存在方式,以重建我们与世界的连接。
敢为人先的现代“巴黎营造”
巴黎的敢为人先并不只存在于本届奥运会开幕式那色彩斑斓的河上盛宴,而是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巴黎传》作者科林·琼斯说,“再没有一个城市像当年的巴黎那样,充满了精力和想象力”。
这其中,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那就是路易十四。他亲政后,法国国力臻于极盛。正是他下令清除所有防御建筑,使巴黎成为一座规划建设中开放的城市,并将观测空间与城市纪念碑式的建筑结合在了一起。“开放取代了惧外,巴黎因此成为现代欧洲史上第一座开放的城市”,美国人若昂·德让在《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中将这一创举看作是“围墙城市迈向现代景观城市的关键一步”,他说,谈论巴黎的发展,人们往往能在一点上看法一致:能引发外国游客好奇的事物不胜枚举,首先便是巴黎拥有只有大城市中心才有的宏伟建筑。
进入17世纪,巴黎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开创性的建筑。部分新建筑的前身,是该世纪中叶巴黎出现的意大利式穹顶建筑,比如40年代的圣路易-圣保罗教堂,或者60年代的四国学院(今天的法兰西学院),这类美丽的建筑改变了巴黎的天际线。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巴黎都是这种创新且法式风格鲜明的建筑的中心。
1671年,路易十四创立了法国皇家建筑学院,在17世纪后几十年有效帮助了开发商和建筑师。比如,在1674年,这个学院的成员讨论如何规定城市广场的比例,以及规定广场附近房子的高度。到了1711年,巴黎城市历史学家费利比安说,在他的时代,“所有外国人”都认为巴黎“是欧洲最伟大的城市”。同时,巴黎的现代技术也深深吸引着外国人,那时的法国已超越曾在城市设施和技术上处于欧洲领先地位的荷兰,连续实现了三个第一:第一个公共邮政系统,第一个公共交通系统,以及第一个街道照明系统。应该说,整个17世纪,每经历重大的规划,巴黎都能从中获益。这种规划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即“品牌再造”。
在1667年,巴黎人和游客已经能在孚日广场(2024奥运会前夕,这里是运动员们的适应性场地)乘上公共马车,把钱交给穿着制服的乘务员,然后坐车到达当地许多景点。如果他们选择在天黑后出行,整个路途中将会有通宵的灯光照亮。当年的一位外国长居者曾在17世纪90年代建议外国人:“无论你来自多远的地方,哪怕只是为了看看巴黎的街灯,都足以促成一次拜访。每个人都必须过来见识一下连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从未想象的一些东西。”
值得一提的还有《巴黎传》中提供的一个巴黎居民比例组成的细节: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巴黎人口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不是巴黎人。也就是说,巴黎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入。早在罗马征服之前,巴黎就已经是一个大熔炉了,这成为这座城市一个长期的历史特征。
重新定义城市的“都市工程”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不同艺术门类的表演者包括空中行走的特技演员开启了一场桥上巡游,这座桥,就是若昂·德让在《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中为其特设一章的“新桥”,他写道:巴黎的创新始于一座桥。
在17世纪,这座桥梁扮演了埃菲尔铁塔今天的角色,那时亨利四世刚征服巴黎,新桥成为他笼络人心的工程,而他亦得偿所愿。历史上第一次,一座城市被一项新型的都市工程(而不是主教堂或者宫殿)所定义。巴黎人,无论贫富,都很快接受了新桥。他们将它视为巴黎的象征以及最重要的景点。
新桥位于巴黎新都市文化最显眼之处,是现代巴黎的首座标志性建筑。随着新桥在1606年进入公众视野,它吸引的游客数不断打破纪录。人们从桥上眺望塞纳河风光,而这种体验自此成为巴黎旅游的精髓。新桥不同于此前其他城市的桥,周围没有房屋,桥上甚至设有小型露台,造型类似剧院的包厢,吸引过桥的人们停下来,倚在桥边,欣赏河面的景色。几乎每一张那个时代的新桥绘画,都充满了在露台欣赏巴黎景观的体验者。从1606年起,新桥周遭的景观不断丰富,许多最新、最美的建筑沿塞纳河而建,使得巴黎成为第一座用河流展示现代建筑面貌的欧洲首都,河岸对美丽而统一的城市天际线的塑造,也在这座城市最早得以体现。而现在,巴黎亦成为全世界第一座用河流实景展示奥运会开幕式情境的城市。
新桥的另一种“前卫”则彰显了与奥运精神相同的“平等”的概念。“由于贵族和贫民都从新桥穿过,巴黎因此获得了其他欧洲首都在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体验,那就是陌生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尤其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接触。”许多17世纪描绘新桥的油画都表达了这种“前卫”的融合,贵族和普通市民一样徒步过桥,新桥成为社会平衡器,桥上人皆平等。
新桥真正塑造了巴黎的都市生活。无论何种经济地位的巴黎人都能走出家门,来到新桥上,享受被宗教战争中断数十载的平静,这里也是巴黎第一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娱乐空间。曾经,这里也一度成为巴黎的戏剧中心,充斥着天赋异禀的街头表演艺人,让人联想起北京历史上的“天桥”。而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新桥演艺,无疑是在重现那段新桥历史。
17世纪旅行指南里的“巴黎漫游”
City Walk(城市漫游)始于巴黎!这是《巴黎,19世纪的首都》《巴黎历史侦探》《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三本书同时告诉我们的。实际上早在1684年,随着《巴黎的奇趣景点新指南》这本旅行指南的出版,巴黎便正式开启了它的城市漫游。
《巴黎,19世纪的首都》和《巴黎历史侦探》两本书中,不约而同谈及一种法式工程——拱廊街,德国人瓦尔特·本雅明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正是一部“拱廊研究计划”合集,这位长期寄居巴黎的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被迫离开祖国,成为一名真正的精神巴黎人,他认为,“巴黎就是19世纪全世界的首都。几乎可以说,巴黎发明了现代城市。”而拱廊街正是城市现代性的缩影。用十多年时间研究巴黎的城市空间,沉迷于拱廊街的画廊、餐厅、古玩店,以及它们精美绝伦的橱窗、玻璃顶蓬与大理石镶板,本雅明发现,一种属于城市化的“闲逛”和商品拜物教出现了,人们在拱廊街很少买东西,因为“他本身就是商品”。
日文版初版于2002年的《巴黎历史侦探》的作者宫下志朗说,“巴黎人的一只脚站在优越的现代世界,一只脚仍留在优美的历史空间里。前者享用物质,后者享受精神。”在高楼还未拔地而起的时代,拱廊街就是巴黎的时尚前沿与购物天堂。这里不仅是戏院、银行、书店的聚集地,更是巴黎人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今,这些拱廊街不再时尚,但“犹如一张泛黄的旧照片”,能够“让人穿越回从前的时光,使人愉快。”书中,在已萧条冷清的拱廊街,宫下志朗找到了保留着19世纪风貌的刺绣用品店,还有柱间拱廊上残存的文字,这都是曾经热闹繁华的证据,被作者视为“无上珍贵的痕迹”。
回溯17世纪末的巴黎,步行探索城市已经成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时尚,甚至上流社会的女性也经常走在街头,不穿戴任何防护,而是穿着最精致时髦的穆勒鞋,令外国人惊叹不已。在《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中,作者又回到有关城市的现代属性的话题中,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能享受步行,是因为在巴黎,越来越多的道路铺设了大卵石,这些油亮亮的卵石赋予巴黎现代的外貌,并且本质上改变了巴黎街道的情调,带给行人一种既新奇又现代的足下体验。
在那个时代,“一座城市之所以值得一游,是因为时下的辉煌和当代的建筑,是因为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丰富的娱乐活动带来的勃勃生机。追求新鲜感和最前沿事物,如艺术、建筑、商业、时尚或饮食的游客,必定会前去巴黎寻找新的体验。他们用在当时看来全新的游览方式,手里拿着17世纪最畅销新颖的城市指南,漫步巴黎街头……而城市漫游者的特权,只有一个自由、多元、创新且包容的都市才能给予。
在文学中不朽的爱之法式浪漫
巴黎何其有幸,世界上大约没有哪座城市像她这样,为无数经典文学艺术作品标榜和记录,从废墟到奇迹,从旅游胜地到大千世界的缩影,戏剧家、小说家、史家、指南书作者、画家、建筑师等等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无数作家使巴黎不朽,或者说,巴黎使无数作家不朽。
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曾说:“任何人与巴黎都不是初见,而是一再重逢。”因为即便是从未踏足巴黎的人,也已经透过文字了解到巴黎的诸多细节。而我们对于这座城市也总是抱有一个真实的刻板印象,即:爱之法式浪漫。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九本与爱相关的文学经典出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一幕,诠释法式浪漫的爱情真谛——
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歌典范、短篇诗集《无字浪漫曲》;缪塞的剧作《勿以爱情为戏》,有人摘抄剧中金句:“我要爱,但是我不要痛苦/我要拿永久的爱情当作爱,我的誓言是永久不渝的”;莫泊桑的《漂亮朋友》,他写道:“人生就像一道山坡,当你向上爬的时候,望着山顶兴致勃勃,但一旦到了山顶,你就会突然发现前面只是下坡和终点,而终点就是死亡”。
2022年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简单的激情》,依然是赤裸裸的生活体验与感悟:“但是,我也感觉到,这一类的动作,这一类的欢愉积累得越多,我们彼此的距离也就越远。我们用尽了欲望的资本。在身体的激情上赢得的东西在时间里失去了”。提前剧透一下,埃尔诺的新书《真正的归宿:和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八月出版;斯利马尼初版于2017年的非虚构《性与谎言》,作者通过采访和自身经历探讨了当代摩洛哥女性的性与社会问题;法国文坛早逝的天才少年雷蒙德·拉迪盖初版于1923年的《魔鬼附身》,书中云:“爱情似乎隐隐约约感到使它偏离的是工作。所以爱情把工作当作是情敌。爱情一点也容不得它。不过爱情却是与人为善的懒惰,犹如霏霏细雨使万物滋生丰盈”;拉克洛的书信体小说《危险的关系》,书中道出一句真理:“只有跟那些我们不久就要舍弃的人,才可以在一起纵情狂欢”;莫里哀作于1670年的戏剧《华丽的情人》,反讽贵族社会爱的虚伪;首演于1732年的皮埃尔·德·马里沃的三幕散文喜剧《爱情的凯旋》,讲述人类情感的复杂。
在《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学者大卫·丹穆若什从伦敦“出发”,第二站即抵达巴黎,他称巴黎为“作家的乐园”,而他所选定的代表这座城市的作家,首推普鲁斯特和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对浸在茶中的那种短短的、圆鼓鼓的、叫作“小玛德莱娜”的点心的回味中,我们寻得那个存在于普鲁斯特的虚构与真实间的巴黎,那是一种记忆中的浪漫之爱,如他所写:“对某个形体的记忆无非是对某一瞬间的遗憾之情;而房舍、小巷、大街,唉!也如岁月一般,易逝难追!”
丹穆若什教授选择的第二位作家朱娜·巴恩斯的作品《夜林》,与《追忆似水年华》一样,有着极强的自传色彩,《夜林》里,巴黎左岸住着一群疯子般的人物,多数是因为之前的情伤才流落巴黎。小说中复杂的情感纠葛碎片化地呈现虚无飘渺的意境,试图告诉我们:巴黎是“失落一代”的失落灵魂的暂栖地,是记忆之地,也是遗忘之地,永远地缠绕着那些讲故事的人。
毫无疑问,丹穆若什要将巴黎的法式浪漫进行到底,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是他选择的第三位巴黎作家。在他看来,巴黎鲜有作家能像杜拉斯那样对早年的创伤挥之不去却妙笔生花,因为她重新创作了自己十五岁时在殖民地时期越南的一段惊世骇俗的情爱故事。当杜拉斯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巴黎重新发现自己作为女儿、情人和作家的身份,她将政治和离经叛道的情事交织在这部梦幻般的小说中。
在故乡曾尝试以爵士乐手身份出道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和他的成名作《美西螈》是教授选定的第四位代表巴黎的作家,2013年,在科塔萨尔的巨著《跳房子》出版五十周年时,它被看作是“一个阿根廷人献给法国首都最美丽的致敬之礼”。巴黎市政厅似乎全然不知有多少《跳房子》的忠实读者每日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脑中酝酿着一张密布书中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文学地图。有多少旅游者去巴黎,是像某些“西班牙版”包法利夫人一样,希望将他们脑中《跳房子》所绘制的文学地图与现实一一对应……但丹穆若什更喜欢《美西螈》,它以巴黎为故事的核心,小说中的叙述者与科塔萨尔一样,喜欢骑自行车去著名的巴黎植物园,而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与植物园中的那只美西螈融为了一体……这个貌似庄周梦蝶的故事,发生在1951年春天的巴黎植物园中。“巴黎”成为为数不多代表真正神秘的词语,拥有独特的氛围,笼罩在魅力的光环之下。
最后在引用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的话,这位文学主人公如此相信梦想:“巴黎是怎样的?无法衡量的名声!她低声重复着‘巴黎’,只是因为重复让她自得其乐;这个声音就像教堂的钟声回荡在她耳边;就像眼前的一束光芒。”巴黎的法式浪漫之爱,永远不会消失。
打卡巴黎的漫画书
●《一点巴黎》
在巴黎,可不要小瞧任何细节!街角的一座咖啡馆,公园里的一把长椅,甚至一间不起眼的旅馆,说不定就和某位响当当的大作家、哲学家、文化人士颇有渊源。巴黎奥运开幕式上塞纳河畔的地标,都是漫画家桑贝笔下妙趣横生的巴黎即景。
●《巴黎有座艺术桥》
卡特琳·莫里斯,法兰西艺术院唯一漫画家院士,带领读者穿越一座幽默的艺术馆,讲述普鲁斯特的灵感来源、蒙娜丽莎被盗事件等趣闻轶事,在这里画家和作家、哲学家之间彼此联结,高冷的艺术评论和学术的文学史料都变得前所未有的生动和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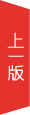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