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
四十年前,我跨过十八岁的门口,第一次独自出了一次远门,从即墨坐长途客车去高密县城的舅舅家。为了让母亲同意这次出行,我寻了一个真实的理由:那阶段身上时常起紫癜,想让当医生的舅母看看。
舅舅家也不宽敞,晚上表姐便带着我去她单位宿舍住。表姐大我七八岁,她身材清瘦,眼睛不大,说话轻言轻语,语气温柔,令人如沐春风。她在前面走,我紧随其后。在家时听母亲说,表姐正在谈恋爱,舅舅不同意,表姐正在和家人闹别扭。看着表姐的背影,我情不自禁地猜想着表姐的男朋友会是什么样子。走到宿舍楼梯拐角处,遇到了表姐的一个同事,没等对方开口,表姐主动介绍说:这是我表妹,从即墨来的。一句:这是我表妹,让我这个从农村来的黄毛丫头,温暖了很久。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接到了表哥的一个电话,想让我当医生的女儿给表姐看看病。表姐病了?一通询问后,女儿便让表姐住进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表姐被确诊为进行性核上性麻痹。这是一种罕见的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疾病,病魔在吞噬着表姐的身体,使她不仅肢体变得僵硬,大脑也变得迟钝。在医院里,第一次看到了表姐夫。他在叙述着表姐的发病过程,讲述着如何伺候表姐的饮食起居。我看到了一个细节,表姐夫在讲述这些过程的时候,手不时地梳理着坐在身边表姐的头发。执手提梳浓情过,却留发丝绕前缘。我没有看到表姐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却见证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美好。表姐已经不认识我了,经过反复地介绍、说明,表姐深思良久,像是从记忆的深处搜寻到了我,喃喃地重复着:这是我的表妹,这是我的表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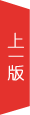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