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有一桩发生在14世纪苏丹菲罗兹·沙阿·图格拉克身上的轶事,缘起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次狩猎:苏丹本人在一个名为托普拉的村子附近发现了一根巨型石柱,它体积巨大,超过40英尺高,表面经过巧妙修饰,上面的铭文隐约可见,苏丹菲罗兹不明其意却深受震撼,思忖再三,决定把它带回德里,安置在自家宫殿中。为此他动用数千名工人,一辆四十二轮车,以及一队客船和驳船,完成了移柱壮举……在这位苏丹心目中,运输和拥有这根古老石柱将永葆他治下的威名,事实也的确如此,700年后的今天,此柱依然屹立不倒。
故事记述于哈佛教授马丁·普克纳所著《文化的故事》里,并未就此结束,菲罗兹不仅考虑到“流长”的未来,也希望探究“源远”的过去,拥有石柱之后,他邀各路学者破译柱上铭文,均告失败,倒是由此生发出有关石柱如何被巨人用作拐杖的传说,后来他干脆自己也在柱上刻录,于是那些未解的印迹上又添加了服务于新目的的神秘信息。
现在我们知道,石柱的建造者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的主人阿育王,他依托石柱,传递佛法与王权结合的新观念,期冀将它们传送到更久远的未来,却忽略了早期的文字终究无法战胜时间的流逝。不过,在他的时代,他已将印度的过去与精选的波斯和希腊“进口”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东西——阿育王的石柱法令。
阿育王与苏丹菲罗兹相隔1600年,发出的信息被后者误读、误用并不奇怪。其实早于苏丹菲罗兹,在公元7世纪,也就是阿育王的石柱信息“发送”约千年后,来自中国的西行取经人玄奘,通过翻译《阿育王传说》,算是模糊理解了铭文的含义,并把它带到了东方。而承载阿育王思想声音的文字要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者征用印度文化时,借鉴挪威学者的研究成果,使用印度-希腊国王统治时期的希腊-婆罗米双语硬币,才得以清晰破解……
古老文化的传送与读取就是如此,总要等待多时空接触与碰撞的机缘。在马丁·普克纳讲述的《文化的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到:罗马人如何从希腊那里借鉴文学、戏剧和神话;日本如何远赴中国学习文本和建筑风格以及新的宗教仪式;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哈伦·拉希德如何将地中海和近东的知识吸收到他的“智慧宫”……这些故事貌似琐碎而庞杂,却印证了文化流动与交互的本质,它们试图告诉我们,“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纯粹的完美自足的整体,它的存在状态即在于流通、混合和再创造。
你无法找到一种纯粹的单一的原生文化,因为文化的演进即是一个如同量子纠缠的彼此影响、交融的过程,诸多非原生的文化碎片被吸纳、重组,其间亦充斥着误读、冲突,甚至暴力、侵占,难以判定原生性与非原生性的确切界线。阿育王从波斯获取他需要的更为壮观的呈现形式,一种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的载体,他也极有可能知道希腊的石柱以及埃及的方尖碑,文化的交融很多时候难以澄清原委;玄奘,马丁·普克纳教授笔下重要的“文化中间人”,则以译者身份偶然完成了另一种非原生文化的迁移与读取,衍生出中国原生文化再造并重新建构的另一个文化故事。
普克纳在书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有时会忘记,文化不是财产,而是我们传承下来以便其他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使用的东西。它是一个庞大的回收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关于过去的细小碎片被回收,从而产生全新的、惊人的建构意义的方式。而我们正是在此过程中发现过去,连接未来。”
始于肖维洞穴的存储与流动
“不同传统被打破成碎片,又被缝补在一起,从而产生无限新意”
有一种受众极广的文化观:地球上的不同人群,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习俗与艺术,他们也必须抵抗外来干扰,守护自己的文化。这种观念将文化视作某种类型的财产,而它属于生活于其中的这一群人。
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克纳试图克服这种单一文化观的局限。他观察到此种观点已在美国本土演化为一种趋势,即便是持不同政见者立场也基本相似:“右翼”想加倍增加西方文化,“左翼”想保护少数族裔文化,人们由于害怕失去文化身份而退缩到各自本土传统中,对其他文化持怀疑态度,反对文化的流通与融合。在他看来,这恰恰与文化的实际运作方式相悖,文化正是由从其他地方借来的东西组成,或者至少是受其影响的。
普克纳教授从最早的人类洞穴开始讲起。位于法国南部的肖维洞穴,展现出人类文化运作的核心机制——数千年间,绘画由粗糙的痕迹变为精心刻画的艺术,相对的封闭让洞穴承载的文化技艺代代流传,它充当了一个具有文化记忆存储功能的设备,一代又一代人类回到此处,合作开展一个他们无法单独完成的项目。而每一代艺术家都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继续发挥,保留并改进前辈的创造。他们也一定试图解释自己所看到的,以自己的文化认知理解遥远过去的创造,以便赋予它新的面貌,并把这一结合体留传未来。
从肖维洞穴,到埃及金字塔、希腊剧院、佛教寺庙、修道院,再到墨西哥的岛上城市特诺奇蒂特兰、费德里科公爵的意大利工作室和巴黎的沙龙,以及博物馆、图书馆,这些生产、存储、革新人文艺术知识的载体都在讲述文化流动与交融的故事。在马丁·普克纳看来,这正是文化史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们需要与过去互动,也要和彼此互动,这样才能让文化充分发挥其潜质,尽管这种互动往往伴随着错误、不解和破坏。普克纳认为,纯粹主义者和清教主义者恰恰是最有可能从事文化破坏行为的人。
在上海书展期间来到中国的普克纳坦陈《文化的故事》是一本文化观念“凌乱”的书,正因如此它才更显有趣,在这本书里,不同传统被打破成碎片,又被重新缝补在一起,从而产生无限新意。正是那些惊动世人的联系和深藏不露的影响敦促人们,在隔离或流通、纯粹或混合、占有文化或分享文化之间做出抉择。
变借用为传统的“后来者”
“罗马人不只是在模仿希腊,他们积极主动、精心刻意地使用希腊文化,从而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文化的故事》中,普克纳教授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深刻表述,那就是:所有的文化都不是纯粹的、原生性的,而是混杂的、交互的结果。它将我们惯常所认知的“文化的交流互鉴”的观念推到了极致。与此相应,书中亦反复出现一个关键词——“后来者”。他说,自己在研究世界文学的时候发现,首创者的角色会特别被给予尊贵的地位,比如人们会强调首个发明者,中国也有自己的“四大发明”,而美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它的文化是从各个地方“借”来的,欧洲也是一个混合性的文化体。于是他强调了一个“后来者”的概念。
罗马人对于一切希腊事物的迷恋或可作为“后来者”最具典型意义的表述。普克纳教授从庞贝古城“梅南德之家”中的雕塑绘画出发,讲述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的碾压式渗透,在他看来,罗马转向意大利半岛本土的文化资源似乎更自然一些,但事实正与此相反,罗马人将一种生成于不同语言,基于不同历史的文化嫁接到自己的本土传统上。
他举了维吉尔利用“后来者”优势创作《埃涅阿斯纪》的实例,维吉尔不仅借此将罗马的史前史与希腊史有机缝合,还编织了一条新的故事线索,体现出罗马人的文化自信:在故事的尾声部分,代表希腊文化的特洛伊人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被意大利同化。《埃涅阿斯纪》作为罗马帝国的建国故事恰恰说明:文化嫁接不仅充满荣耀,而且蕴含无限可能,采用微妙策略,并不代表“后来者”身处劣式。
这里顺便要提及的是,在陈嘉映作为希腊文化入门文本的小书《希腊别传》里,则提及了希腊作为“后来者”的身份,作者告诉我们,实际上希腊最初也处于智识的洼地中,也是从周边的几个古老文明里“师夷长技”,比如从巴比伦人那里学到了数学和天文学,从埃及人那里学到雕塑和医学,从巴比伦和埃及那里学来几何学。就连希腊神话,也有外族来源,这是希罗多德说的,几乎希腊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进口”的。还有伟大的《荷马史诗》,也并非原创,而是闪现着中东更古老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影子,希腊人自称学生,并不全是谦辞。这样看来,罗马的“全盘希腊”,似乎也是在走某种学习的捷径而已。
回到《文化的故事》这本书,普克纳教授特设一个章节,致敬另一位“后来者”,他心目中的英雄玄奘。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的佛教传统也是“后来者”,而这个“后来者”却创造性地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故事,这其中作为取经人和译经者的玄奘功不可没。书中,普克纳称玄奘为“文化的中间人”,他说:“作为文化中间人,玄奘不能只赞美一种外国文化,他还必须称赞目标受众的文化,他们身在中国。”在他的游记中,他引用孔子关于“正名”的重要性来解释自己为何希望获得更准确的佛经版本。从那时起,寻找更可信的基础经文和更加准确的译文便成为人文学科的要义,这使他成为中国人文知识传统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人物。玄奘正是那个追随“进口”文化回到源头的“后来者”。
普克纳还特别提及了意大利语里“翻译”与“背叛者”这两个词极为相近,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文化的“后来者”的某种焦虑与竞争心态。
关于未来的文化保存与传送技术
“公元2114年还会有图书馆吗”
在《文化的故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普克纳教授向所有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公元2114年还会有图书馆吗?事实上,积累、储存和分享知识的技术载体,贯穿了全书:建筑材料、纸张、文字,通信技术、印刷术、游记、日记、笔谈、评论、书目编纂、口译,以及古希腊的学院、印度僧侣团体、阿拉伯的智慧宫、中世纪的修道院和抄写室、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室和大学、现代的博物馆、沙龙、未来的图书馆……在他看来,所谓未来的图书馆,便如同阿育王所使用的铭文石柱,都是基于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技术性支撑而已。但他同时表示,仅有技术的支持是不够的,因为文化的保存与传送,其实要建立在一种可持续的文化机制基础上。当年阿育王正因为过高估计了文化的技术功能,而没有建立起阅读这些铭文的知识教育体系,才使得文化信息的传送宣告失败。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使用技术,又如何去建立传承文化知识的相关机制。
在上海书展期间,马丁·普克纳教授特别以一场演讲来推介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未来图书馆项目,这是一个始于挪威奥斯陆的艺术项目,由一位苏格兰艺术家创建。从2014年开始,每一年凯蒂·帕特森都会邀请一位作家将一本原创文学作品保存在这个未来图书馆中,但其内容要等到100年之后才能阅读。第一位受邀作家是全球读者熟悉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图书馆指向了100年后的未来,所以凯蒂也想象到一种可能性,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不知道怎样去印刷书籍,不知道怎样以纸质的印刷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了。所以在图书馆中,不仅保存文学故事,还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指导人们如何从技术角度来印刷,装订成书(令国人欣慰的是,这两种发明都来自中国)。未来图书馆里建有一个很小的储藏室,看上去像是一个洞穴,书籍保存其中,这个小房间周遭树苗环抱,百年后成林,而那时一些树木会被砍下,用于制造纸张,它们将用来印刷制作保存的书籍。
据此,未来图书馆呼应了书中的许多重要主题,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便是文化的保存,人类需要以创造性的手段储存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未来的世代,这是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而在技术制胜且迅猛更迭的未来,这将变得更加重要。2114年,当未来的人类进入那个图书馆“洞穴”,他们也会如同进入肖维洞穴的一代代“后来者”一样,试图理解其中存储的内容,并留下有关自己新的信息。
必须提及的是,普克纳也据此传递了他关于文化技术演进的观点:媒介可能有先后,但没有高下,传统的媒介不会也不应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活,比如存储于未来图书馆中的纸书。120年前,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提出“乐愈进则苦亦愈进”的理论,认为事物的发展并非单一的进步,而是对立因素的共同增长,以此来否认进化的发展观和单纯的文化进步主义。与此异曲同工,普克纳教授也试图让我们意识到,技术的演进也会让我们遗忘过去以及彼此,由聚合走向离散。当我们与AI对话时,实际上是在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对话,我们的交谈者或者我们在交流的东西,实际上是阿育王所代表的历史,是玄奘所翻译推介的历史,是巴格达的智慧宫当中所收藏的所有文本,以及未来图书馆中珍藏的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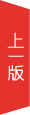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