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勋祥
“我自知我不是英雄,有时甚至脆弱。但极地是我的老师,告诉我如何成为‘英雄’,让我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奋斗的光荣。”
不断漂移的北极冰,也给人启迪:“我多次踏上北极点,随即又漂离了它。昨日的辉煌已慢慢淡去,我们必须开始未来的奋斗,停止了就会漂离目标。”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赵进平是极地的“熟客”。
30岁时,赵进平参加了中国首次南极考察;41岁时,他参加了由中国科协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45岁时,他又参加了中国首次北极考察(政府组织),成为中国第一位登上南北两极的科学家。多年来,他先后16次前往极地考察;如今,古稀之年的赵进平仍在从事极地研究工作。
2024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作为纪念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雪龙”号科考船停靠青岛并举办为期3天的开放日活动,供社会公众参观。“雪龙”号是我国最大的极地考察船,也是我国极地考察的主力船之一。过去多次开展极地考察,赵进平乘坐的就是这艘科考船。
4月12日,赵进平登上“雪龙”号参观,再次见到“老朋友”,他感慨万千。回顾那些难忘的极地考察日子,赵进平这样描述:“像翻阅掀过的日历,像是观看身后的脚印。”他一直认为极地考察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正因如此,赵进平非常珍惜这次参观机会,即使重感冒尚未痊愈,他也带病前往,“怎么也要上船看一看”。13日,在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海洋与大气学院240室接受记者专访时,赵进平还会偶尔咳嗽几声。
在海洋与大气学院,紧挨着240室的,是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海洋大学海洋调查实验室,这里保存着不少海洋调查“老古董”。赵进平打开实验室大门,向记者介绍一台曾用于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MARKⅢ型温盐深仪(CTD)。“当时,这个仪器在全国只有3台,另外两台不能外借,考察组织方只好向中国海洋大学(当时叫山东海洋学院)求助,并答应给3个赴南极考察名额。”赵进平告诉记者,经过自愿报名和选拔,他成功入选,从此和极地考察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的一生有时就是这样,充满机缘巧合,赵进平上大学也是如此。初中毕业后,他进入吉林省机械厂当机修工人,后来厂里有了6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又有2人放弃了推荐入学的机会,因此他得以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但机缘更青睐有准备的人。1980年,赵进平考入山东海洋学院攻读物理海洋专业硕士,1983年留校工作,毕业后随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侍茂崇从事近海调查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为他参加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考察“加了分”。赵进平也是我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中学历最高的考察队员。
“探索未知海洋世界,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在经历了中国近海调查特别是首次南极考察之后,赵进平的内心被极地世界占据了,此后他又陆续参加了15次极地考察,最后一次探索极地是在2016年。时至今日,他仍认为,“只要有条件还是应该到现场”。同时,他也遗憾随着年纪增大没有机会再去极地,“不要帮不上忙,还给别人添了乱”。
虽然不再到达极地考察现场,但赵进平并没有赋闲,自始至终在带队伍、做研究。中国海洋大学与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于2007年7月签署协议共建的“极地海洋过程与全球海洋变化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与高校共建的三个实验室之一,赵进平担任实验室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实验室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建立起一个实力雄厚的极地科考研究团队。自2007年至今,中国海洋大学每年都有师生参加极地科考,在海冰、大气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眼下,赵进平正在为自主研发的海雾光学剖面仪做最后定型、推向市场的冲刺准备,该仪器依靠气球的浮力可以飞到近5000米高空,从而获得自海面至到达高度之间的海雾/低云垂向光学结构,是国内外独创的海雾观测新手段,已在2018年第二次中俄北极联合科考、2020年中国第11次北极科考中应用。“我们研发这个仪器已经很多年了,对它寄予很大期望。目前仪器正在千里岩岛上进行试验,目标是今年定型,尽快推向市场。”赵进平表示,该仪器将在今年北极考察时再次应用,“这个仪器在极地非常有用,因为在极地航行,航道上经常有雾。深化对海雾的整体认识,将更好地为极区生产活动、航道利用以及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极地考察研究,支撑赵进平的是什么?他说,每次完成极地科考回国,科考队员总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这时谁都耻于谈论在极地身心俱疲时的沮丧、情绪低沉时的懊悔。“我自知我不是英雄,有时甚至脆弱。但极地是我的老师,告诉我如何成为‘英雄’,让我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奋斗的光荣。”赵进平告诉记者,不断漂移的北极冰,也给人启迪:“我多次踏上北极点,随即又漂离了它。昨日的辉煌已慢慢淡去,我们必须开始未来的奋斗,停止了就会漂离目标。”
自找苦吃 首次南极考察
记者: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给了中国海洋大学3个名额,您当时是带着什么想法报名的?
赵进平: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国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议,掀起了出国留学热潮。1984年,当中国海洋大学获得3个南极考察名额时,学校规定国外留学和南极考察只能选一个。在中国海洋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就跟着老师参加过近海调查,对海洋充满了向往。所以得知有去南极考察的机会时,我觉得非常难得,毅然报名。当时心想,国外留学,何时不能去?
记者:首次南极考察,对于团队、对于个人都经验不足,您有什么顾虑吗?
赵进平:我相信很多人是怀着面对更大艰险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思想准备的。这是有背景的。从南极考察研究来说,《南极条约》约束各国在南极洲这块地球上唯一一块没有常住人口的大陆上的活动,确保各国对南极洲的尊重。1983年5月,我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之一。但缔约国没有表决权,一到关键事项时就会被“请出”会场喝咖啡。所以,要深入参与南极考察研究,就必须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通过首次南极考察,我们建成了长城站,获得了南极宝贵数据,也实现了这一目标。
所以大家都深知此行意义。出发之前,我们签了“生死状”,包括后来参加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中国首次北极考察也是这样。我常说这是去“自找苦吃”,但吃苦不是目的,支撑我们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的责任感。
记者:当时使用的是“向阳红10”号开展南极考察,科考船没有破冰能力,也不够先进。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长郭琨在《首闯南极的日子》一书中记载,考察工作遇到了很多危险。
赵进平:确实是这样。因为是首次南极考察,没有多少经验,“向阳红10”号上甚至备有一些大的塑料袋,准备队员万一牺牲了就装里面,然后放在船底冷库冰冻起来。在考察时,我们遇到了极地气旋风暴袭击,“向阳红10”号犹如一叶扁舟,剧烈摇晃。当听说科考船后甲板上的MARKⅢ型温盐深仪等设备被巨浪打翻,很可能被大海吞噬时,我们几个人赶紧去抢救。这时一个海浪打过来,海水没到了脖子处,差点把我们冲到海里去。当时我也不害怕,只想把带来的“家底”给保住。后来提起这事,倒一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从零开始 首次远征北极点
记者:首次南极考察后,您为何多年没有再参加极地科考?
赵进平:首次南极考察的第二年,国家海洋局就购置了一台MARKⅢ型温盐深仪,因为不再借用中国海洋大学的调查设备了,所以也不给学校南极考察的名额了(笑)。
记者:直到您去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做博士后,参加了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
赵进平:是的。这次考察是民间赞助的,由中国科协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时间是1995年。这时,我国已开展了10余次南极考察,相继建成了长城站、中山站,但对于北极考察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记者:您在《情系北冰洋》一书中专门记载了这次考察,当时是靠滑雪和狗拉雪橇到达的北极点。
赵进平:没错。1995年4月,我们一行7人乘飞机来到北纬88度的冰原上,加入到美国的一个团队中,他们主要充当向导。当时,我们个人背着生活用品靠滑雪前进;另外雇了两个雪橇,每个雪橇由10条爱斯基摩犬拉着,上面装载着帐篷、炉具、燃料、通讯设施、考察仪器等。我是唯一的海洋工作者,肩负着所有海洋考察任务。白天滑雪前进,晚上抽出时间开展北极考察。经过13天行进,最终到达北极点。
记者:因为不能携带重型装备、考察时间有限、活动范围不大,本次考察其实受到了极大限制,更像是探险性的。
赵进平:北极考察涉及的学科很多,绝大部分考察项目都不可能在徒步的状态下完成。可以说,我们当时是用最原始的方式开展了一次探险式北极考察,却是尽了全力。我们一般上午10点出发,凌晨2点安营扎寨。当大家都休息时,我常常滑雪去找适合考察的冰面,用斧子砍出冰孔(直径40厘米左右),下放仪器。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了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等方面的观测和取样。
当晚上有考察任务时,我实际上睡得很少。严重的、超乎想象的疲倦困扰着我,浑身疲倦得像要散了架。但全队不会为一个人而休息一天。我们再累也必须搭帐篷、套狗、捆雪橇、做饭。
记者:这次北极考察有什么意义呢?
赵进平:这是一次拓荒性的考察,使我国成为“在北极实质性开展科学考察”的国家。基于此,在1996年召开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年会上,中国向大会正式提出了入会申请。经过讨论,我国被该委员会正式接纳为成员国,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第一个北极圈以外的国家。我们从零开始追赶,与许多发达国家的科学家一起,站在了探索北极的同一平台上。
开拓创新 助推极地科学发展
记者:参加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对您的事业产生了什么影响?
赵进平:可以说,影响非常大。1999年,我国正式组织了首次北极考察,对北极的考察研究真正揭开序幕。在我国首次北极考察航次中,采用了南极考察15年的全部经验和积累,用上了“雪龙”号等当时几乎所有先进的考察手段。在我国1999年以及后来2003年、2008年和2010年的四次北极考察中,我都负责海洋组的工作,我总是想方设法地增加考察站位,抓紧时间尽可能地多做项目。因为我经历过难忘的冰面考察,知道获得一点北极的数据是多么艰难,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生命的代价。
记者:40年来极地考察中,您带领团队开展了哪些开拓性工作?
赵进平:大家都在极力开拓,更希望看到我国的高技术成果能够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也做了一小部分工作。例如,2003年,我们在白令海峡成功布放潜标,它能通过布放到海面以下的各种传感器长期观测海洋环境要素,这是我国开展极地考察以来第一次布放潜标;2015年,我们研发出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冰基海洋剖面浮标,实现了对北极气-冰-海环境全年实时监测,使我国的北极考察从夏季考察进入全年考察的新阶段,大大加强了我国的北极考察能力。
记者:创新性发展北极考察的方法和手段,您提出并研发的探空气球携带的海雾光学剖面仪也是其中代表。
赵进平:北极光学观测一直是我的兴趣,这项工作坚持了10余年,并通过多个极地国际合作航次开展了系列应用,使我国成为北极光学观测数据最多的国家。例如,2007年,我参加了加拿大冬季北极考察航次,首次开展了海冰侧向光衰减观测和研究;2014年,倡导并组织了北极海雾光学剖面观测,靠大型气球携带光学仪器探测海雾,是世界上靠光学手段考察海雾的首次尝试。
对极地海雾开展观测和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2019年,“雪龙”号在南极的密集冰区里航行,意外与冰山碰撞,险些酿成安全事故,正是受到了浓雾影响。因此,深化对极区海雾的认识,可以更好地为极区生产活动、航道利用以及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记者:古稀之年,您仍然在极地研究领域开拓创新,未来您有什么打算?
赵进平:极地考察给了我永恒的记忆,今天回忆起来感觉还在昨日,过往种种时时激励着我。在有生之年,希望还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和年轻人一道,发展我国的极地科学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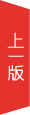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