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郭爱克,每天如常早早走进办公室,桌上高高垒着两摞书,其中一本《新德汉词典》尤为醒目。37岁时,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获得德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如今,他的办公室仍弥漫着喂养果蝇所需的特殊气味,这是他多年来研究的方向。
53岁那年,郭爱克才开始迷上果蝇研究。赴德国前,他还特意去北京王府井配了一副老花镜以备看清小小的果蝇。面对外界的不解,他坚信科学兴趣更重要,转换研究方向并未让他纠结得失。
2003年,郭爱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去年11月,他的学生李岩及其团队首次将果蝇送上中国空间站开展太空实验,他特意佩戴了当年当选院士时的枣红色领带以示庆祝。
谈及37岁读博的经历,郭爱克表示,那是“救了我一把”。1959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国家选派到苏联留学,五年后回国却遭遇了“文革”十年。37岁赴德国进修,他下定决心抢回丢掉的10年,践行“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名言。在德国,他以“特优”的总成绩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拿到的第一个博士学位。
郭爱克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丽蝇视细胞的光谱和偏振光灵敏度的电生理研究》。毕业时,德国实验室的朋友们为他戴上了特制的博士帽,帽子上方是一只丽蝇模型。回国时,他还受到了老所长贝时璋院士的接见。贝时璋也是一位曾在德国留学的学者,他们除了师生关系,还有一样的德国情结。
53岁时,郭爱克决定转换研究方向,开始研究果蝇的学习记忆。契机是在1992年的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他听到了一位德国教授的报告,被果蝇的学习记忆能力所震撼,当即决定与其合作。回国后,他在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果蝇学习记忆实验室。
得知果蝇即将登上太空的消息时,郭爱克感慨道:“就像当年送子弟兵过鸭绿江一样。”他深知这一实验的科学意义,对探讨生命起源和智力演化具有启示意义。他也深知这一实验的艰辛,但团队还是千辛万苦把果蝇“捧上天”。
现在,郭爱克每天的工作节奏与年轻时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荣誉讲席教授,他在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有院士工作站,工作无缝衔接。工作之余,他喜欢看看书画、听听音乐,并认为好的科学研究在哲学上一定是好的。
郭爱克的长寿或得益于遗传基因上的优势,其母活到100多岁。他和夫人丰美福研究员大半辈子都吃单位食堂,习惯简单的生活。
谈及学术热情,郭爱克表示,他从老科学家身上看到了“科学家精神”,并养成了这样的工作习惯。他敬仰的科学家是钱学森,追求的是有益于人民的成功。他寄语科研后辈要“敢为天下先”,有勇气做困难的工作,并深信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只要努力了、尽力了、做到最好了,并有益于人民,就是一种成功。 孟凌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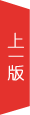



 前一期
前一期
